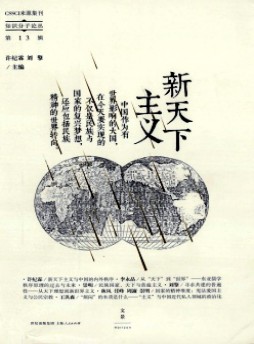知识分子与产品质量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知识分子与产品质量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本文从政治语词/概念入手,讨论知识分子如何提高他们所供给的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一方面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制造“封建主义”的语词/概念混乱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说明分析、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基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某些政治语词/概念具有示范意义的清理工作,归纳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语词/概念意义澄清
一、知识分子提供政治符号产品时的责任问题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在人们的言述中,“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①既然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语词的时候,概念意义的含混与价值评判的分歧并行而来,那么,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妨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规范性的与描述性的。
“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它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②“道德理想的捍卫者”、③“社会的批判者”、④“无私无畏的英雄”、⑤“精神的超越者”、⑥独立的“业余爱好者”⑦等。可以说,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⑧
“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则有所不同,它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从这种角度来看,李普塞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视为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⑨据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符号世界的操作者。与此相类似的定义是萨义德提供的:“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artof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⑩如果说李普塞特和萨义德的定义显得有些笼统或过于宽泛,那么,哈耶克给出的判断则较为具体: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尖刻,不过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判断,它揭示了知识分子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客观事实:“知识分子与弄‘观念’这套东西是几乎不可分的,至于观念是属于理想主义或唯物主义,……皆不关紧要。”依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亦即理念人。
如果我们在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符号产品的供应者,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是否总是人类的福音?是否曾经成为人类灾难的序曲?毫无疑问,前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对此,已有知识分子显示出清醒的反省意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波普尔在审视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作为时,就曾经颇为自责地写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如果说波普尔的反省主要针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批判的自我反思就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每一次和平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都和这个民族失之交臂,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意识形态的力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既然近代以来的中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那么,在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中,究竟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符号产品危害最大?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政治性的观念或者政治符号产品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危害也最为剧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萨托利等人的诸多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该问题答案的某些方面。比如韦伯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著名划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人物,但它同样适用于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尽管支配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然而,知识分子却不能奉行“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不能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必须遵循责任伦理,“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同政治人物一样,放弃信念伦理的精神执着,“采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
不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要减少或者避免自己在传播、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仅仅在行为取向上奉行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比如,调整政治思维、完善政治知识、清洁政治语词/概念等。本文的着眼点是政治语词/概念的分析与澄清。
二、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封建主义”为例
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词、概念,要以某种语言作为传播交流的工具:“每位知识分子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就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然而,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事物与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我们周围的现实,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实际上,语言有助于构造这个世界本身。”换言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
具体到语言与政治的关系上,“语言就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政治的武器。”一方面,作为政治传播的工具,政治语言既有准确地表达政治观念、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之功能,同时也有可能给政治传播、政治交流带来障碍。“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的武器,政治语言可能被用于维护基本人权、伸张政治正义、批判专制统治,但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成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牟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
在语言(包括语词/概念、符号)与政治如此复杂的关系格局中,知识分子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来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这样,知识分子在操作、使用政治语言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否则,其后果不只是笑话、混乱,有时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此仅以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政治词汇———“封建主义”(feudalism)为例,以说明之。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封建制存在于秦汉之前。故历史上有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说。把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封建主义”的概念“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的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因为概念与名辞的错乱,‘’中还发生过要大家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而居然把它改为《分封论》的笑话。”
问题在于,“封建主义”这个政治语词/概念在使用上的错乱和笑话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此厘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强调知识分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因为“封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指的是“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赐人”,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情形。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要发生在西周时期。然而,“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却于20世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手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相反认为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
这种根本性的转折非同小可:它不仅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更重要的是它以西语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为概念工具,不仅提供了一套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社会政治观念或者符号产品———“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以“封建主义”语词为中心,包括诸如“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思想”等在内的庞大的语词、概念系列,迄今它们依然流行于学术论著、学生教材、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之中。
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由一些知识分子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政治语词、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而且给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的要害在于对西方文献(包括马克思的著作)中“feudalism”的误读、误用、误导。在西方文献中,“feudalism”的含义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四处分散的社会结构”。然而,把作为“feudalism”之翻译的“封建主义”运用于中国自周代、尤其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分析时,这种“封建主义”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恰恰与“feudalism”在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情形相反,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社会结构。”这样,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来指称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时候,确实正好弄了个张冠李戴!而且,正如识者所言,这种语词概念的混乱“延续甚久,影响极深,从本世纪初一直到本世纪尾。……列出因‘封建社会’概念的误读误导误用而产生的思想、认知和政治实践的阴错阳差,就差不多等于是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如果说得更尖锐一些,这些流行于现代汉语中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政治词汇不仅发挥了误导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欺骗性含义”。所谓“欺骗性含义”是指,“即使词语只有习惯用法中的含义,如果说话者不用它来指听者赋予它的含义,那么这个词语就会是欺骗性的———被欺骗性地使用。”不幸的是,在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中,具有“欺骗性含义”的语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当然,在现代汉语中出现诸如“封建主义”之类的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及具有“欺骗性含义”的政治词汇,并非都是知识分子的过错。不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政治语词/概念既然与其制造、解释的政治观念、提供的政治符号产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
如果说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多半是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知识分子对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责任,而且力图把这种责任意识转化为明确的态度、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在态度上,他们主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既不应当接受、也不应当散布引起迷惑的词———肯定会造成欺骗的词。”在行为上,他们着手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在《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一文中,哈耶克仔细地区分了七对关键性的语词/概念,旨在澄清其中的歧异与混乱;萨托利则把写作《民主新论》归结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力图揭开笼罩在“民主”语词/概念上的迷雾。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据此,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其一,语词/概念不能任由我们赋予意义。
知识分子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他们在使用语词/概念的时候,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力图突破语言的限制:知识分子“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正是出于突破语言藩篱的天然倾向,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约定论的意义理论:语词的意义仅仅是约定的,一切定义说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们任意规定。然而,约定论真的可以为知识分子任意规定语词的意义提供依据?按照萨托利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就理论而言,约定论的根据是脆弱的。约定论基于语言意义的约定俗成和语言惯例,认为既然语言的意义与约定有关,而任何定义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约定,那么,对语词概念的定义就是任意的。然而,“任意性非但不是定义过程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它还是这样一项评判标准: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某个定义是错误的或是无用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政治语词/概念。举例来说,如果“民主”一词可以任意定义的话,那么,不仅这种定义是无用的,“民主”的语词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实践来看,约定论的后果是有害的。“任意的定义只能破坏语言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从而使一个交流(同时也是组合现有知识的)工具变成十足的制造混乱的手段。”这种情形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尤为典型。举例来说,上述“封建主义”语词/概念的混乱就与作为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进行任意定义有关。
作为知识分子的萨托利曾特别告诫知识分子:“如果词语从根本上说可以任由我们赋予意义,我们便只能向巴别塔前进了。这时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个充满语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会,他们靠着耍弄语言和意义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负众望。”因此,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第三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是任意定义语词/概念的意义以成为语言巫士,还是遵循语言游戏(包括定义这种游戏)的基本规则?
其二,在语义场中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
所谓“语义场”,按照萨托利的说法,乃是一系列相近或相关术语结合而成的一种语义结构,在一定的语义结构中,某些相近或相关的语词/概念彼此关联、相互牵制,以致不能轻易改变其中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词语(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物,它们共同处于由一系列相近和相关———亦即结为一体的———术语组成的语义场,因为其中每一个术语的再定义(意义的变化)都会导致对某些甚至全部有关术语的再定义。”
由于语义场的结构性限制,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就不能背离其他相关语词/概念的定义。否则,将破坏语义场的稳定性,从而导致其他语词/概念意义的混乱。比如,定义“权利”会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语词/概念如“资格”、“自由”、“利益”、“正当”、“权力”等等,而这些语词/概念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利”的语义场。正是这一语义场锁定了“权利”这一语词/概念的基本用法及其核心意义,从而为识别、排除对“权利”的任意定义提供了大致的标准。由于语义场具有结构性的语义限制功能,借助语义场可以对语词/概念的定义进行检验。根据萨托利,语义场的检验有两条判别规则:“如果对一个术语的定义打破了该术语所属的语义场的稳定,这个定义就应当表明:(1)没有一个‘语义场意义’被排除在外;(2)全部‘语义场歧义’(模糊、无限制、混乱)没有被进一步加深。”如果按照这两条规则,上述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定义就不能通过有关“封建主义”(“feudalism”)语义场的检验,因为它不仅已经将西方文献中构成“封建主义”语义场的一些基本的语义场意义排除在外,而且大大加深了“封建主义”语义场的歧义与混乱。
其三,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如果说通过语义场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是从语言系统内部来避免任意定义所引起的意义混乱,那么,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的检验则是从外部入手来减少语词/概念的混乱与欺骗性。所谓“从外部入手”具体说是指诉诸经验、诉诸历史:让经验与历史成为检验语词/概念的试金石。这是因为语言首先是以往经验和知识的宝库,是经验积累的保管者;另一方面,“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反映了概念发展史的检验。”只有参照经验与历史,才能揭破政治语词/概念的歧义性与欺骗性。
在此我们不妨以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以拒斥“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为例来进行说明。根据熊彼特的分析,古代民主理论有两根支柱———人民的意志和共同的福利,前者被视为是政府权威的来源,后者则被归结为政府权威的目的,据此民主概念的内涵被确定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通过选举集合人民意志的制度安排。在熊彼特看来,这种古典民主理论得不到经验分析的支持,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而且,古典民主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根本颠倒了两件事情: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这成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选举代表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民主实践的经验事实来看,民主的关键恰好在于把二者的优先顺序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民的实际作用不过在于产生一个政府,选出社会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基于此,熊彼特拒绝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把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熊彼特不仅依靠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检验进而否弃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且为建立一个经验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在政治语词/概念的丛林中,散布引起迷惑的语词、制造概念混乱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那么,分辨、识别他们也非难事。因为,他们不过“是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事实,即词语是经验的容器,或者说是经验的载体。”因此,对付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像熊彼特那样,让他们的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其四,在语词/概念之间进行区分。
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是划分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语词/概念:前者描述客观事实,涉及“是什么”;后者蕴涵价值规范,体现“应是什么”。比如,“民主”一词虽然容易导致混乱,但由于它本身“不但有描述和指谓的功能,它也有规范和劝导的功能”,因此,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应是什么的规范加以区分,不仅大大有助于澄清民主之语词/概念的混乱,而且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民主定义提供了可能:“界定民主的问题包含着双重内容,它本身要求一个描述性定义和一个规定性定义。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时它们也不能互相取代。”尽管在描述和规范之间可能难以划出严格的界限,但这并不损害二者的区分对于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重要性。
另外一种区分则是透过语词/概念所指称的不同对象及其不同的性质,以展示语词/概念的区别。比如,根据哈耶克的分析,许多人所习惯使用的同一的“法律”(Law)这一语词/概念实际上是在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一是内部规则,它是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划定了个人受保护的范围。”这是社会在长期的演化中自发形成的规则,是自由的法律;二是外部规则,这是“只适用于特定的人或只为制定规则者目标服务的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尽管这种‘法律’必须由那些受委托执行它的人来执行,但是它不能因此而成为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共同使用着“法律”(Law)这个语词/概念,为了避免混淆,哈耶克主张采用两个古希腊的语词/概念来分别指称二者:用“Nomos”表示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用“Thesis”表示外部规则———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许有人不赞同哈耶克对“法律”这一语词、概念的如此划分,但就避免语词/概念的歧义与混乱而言,其方法论的示范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①③⑥[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3、2页。
②⑤⑦⑩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14、71、17、29页。
④⑧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583页。
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邵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233页。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王小波等著、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8页。
季红真:《世纪末的回顾》,载《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第301-302页。
参见《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33、234页。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108页。
钱永详:《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00页。
在某种意义上,波普尔主张政治理论需要从单纯关注“谁来统治”问题转向关注“如何统治”的问题,可以视为是对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政治思维的一种忠告。参见波普尔《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载《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第482-483页。
Heywood,A.(1999).PoliticalTheory: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css,Inc.P2.
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奥威尔(George0rwell):《政治与英语》,转引自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30页。据丁学良先生介绍,他曾于1992年冬和1996年末两次向两组西方比较历史学者和社会学家提问:“在各位的观察中,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概念最走样、亦即最扭曲的理解,首当其谁?”这两组完全不同的西方学者均首推feudalism。
参见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开放时代》1998年11、12月号,第46页。
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参见《嵇文甫文集》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45、548页,序言第4页,第4、295、296、4、295、296、298、297、8、9页。
参见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
[美]理查·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德论后现代》,载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Heywood,A.(2000).KeyConceptsinPolitics.NewYork:Palgrave.P5.
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365页。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