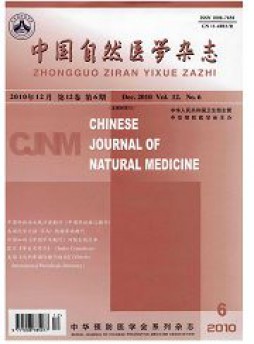自然教育观的跨文化对视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自然教育观的跨文化对视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
《爱弥儿》与《庄子》虽属不同语境下的多维性专著,但它们都有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论倾向。因文化时代背景各异,“自然”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内涵。将卢梭与庄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横加比较,二者虽因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诉求,但我们也会惊喜地发现卢梭和庄子的思想有着微契合之处。厘清两位哲人的自然教育观,对现如今教育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
《爱弥儿》;《庄子》;自然教育
教育本是一个多向度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生发的一系列教育原则是教育施行的依据。艺术、社会、自然都是教育的向度,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对人情感的陶冶、健康审美力的培养与健全人格的塑造都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与审美发生联系就具有了升华的维度,美育成为了现如今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被人们全方位地解读与发掘。自然教育是美育的一个扇面,自然教育原则在各种思想体系中又有不尽相同的内涵。笔者选取先秦时期道家哲学的代表性著作———《庄子》[1]与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卢梭的作品———《爱弥儿或论教育》[2]来进行跨文化的探视,这对我们理解自然教育丰富的内涵有较大的启示。
《庄子》与《爱弥儿》是分属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在那个“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的社会,《庄子》这本书的思想意旨本就是复杂的。它的确是一部哲学专著,庄子站在道家哲学元范畴之上提出了如何“体道”的主张。但《庄子》的富饶让我们不得不对这样一部寓意丰赡的书产生拓展性的理解与诠释。在回归自然的“体道”中,庄子以神话隐喻的独特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怪诞的世界,美国学者爱莲心就认为《庄子》中的神话与隐喻形象的使用并非庄子无意的安排与拨弄,而是庄子有意为之的哲学策略,以此来实现庄子所要达到的哲学目的。“《庄子》文本中的不连贯和十分难解的文学方式跟达到自我转化的目的技术手段有一种系统的关联”[3]。庄子假借一系列怪诞的意象是与实现读者心灵转化的哲学意旨分不开的。虽然庄子没有明确提及此书是写给受教者的教育专著,但我们有理由从教育的角度去解读《庄子》。阅读本就是人对德行的自觉追求,庄子也成为了逻辑上的教者。况且,庄子的思想是有教育诉求的,在《庄子》中充斥了大量人物对话与独白,这往往给读者以另类的启示。特别是其以“游”的方式来完成对“道”的体悟,这种对人们直觉(诗性智慧)的唤醒与自然美育的原则暗中契合。卢梭的《爱弥儿或论教育》是启蒙语境下的产物,卢梭所处的时代是崇仰理性的时代,理性主义的过度猖獗让卢梭生发了培养“自然人”的想法。在卢梭看来,社会的“种种成见、权威、强迫、规范,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人的自然天性”(《爱弥儿》)。那么,回归自然,用自然教育的原则来培养作者假想的儿童———爱弥儿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发现,卢梭明确地表示这本近小说似的作品是他对教育的论述,较之《庄子》有着更为明确的写作目的,即对教育的看法与评解。
1762年,在相继发表了早期两篇论文之后,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卢梭也多次强调《爱弥儿》在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致友人马勒萨尔伯的信中,卢梭说:“我的全部精神智慧分散于前两篇论文和《伦教育》中,三部著作不可分割,构成一个整体。”[4]前两篇论文指《论科学与艺术》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尤其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就敏锐地洞见了那个时代技术与文明对人类早期纯朴情感的破坏,充满了卢梭对科学启蒙及其后果的审慎思考。所以,我们在解读《爱弥儿》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论科学与技术》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两篇论文对《爱弥儿》的思想预设,这是进一步理解《爱弥儿》的先行前提。早在《爱弥儿》出版之前,《社会契约论》就出版了。此书一出版卢梭旋即被指控是在“攻击各国政体”。然而,卢梭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紧随其后出版的《爱弥儿》的注释性附录。还说《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爱弥儿》引用和改变了了《社会契约论》的许多东西[5]。由此可以想见,《爱弥儿》绝非一部单纯的教育论著,而是和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联的(《社会契约论》明显谈的是民主政体及其法律制度建设的问题,因此是关于政治制度设计和立法的书)。况且,一般认为,《爱弥儿》在有意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书的开篇不久卢梭就写道:“你要想懂得公共教育的理念吗?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吧。这可不是一部政治作品,像仅凭书名来判断的人所想的那样。它是从不曾有人写过的最佳教育论。”
我们可否断定,卢梭写作《爱弥儿》和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有着相反的意图。《爱弥儿》不仅是一部论教育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阐扬卢梭政治主张的专著。由此观之,《爱弥儿》中的自然教育至始至终都秉承面向社会、面向政治的教育原则,卢梭成为了自然教育原则的操控者。自然的教育,是《爱弥儿》的行文起点。在第一卷卢梭就告诉我们,他这部小说主要论述“自然人”的培养。他说“:一句话,必然了解自然的人。我相信,人们在看完这本书后,在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有几分收获。”所谓“自然人”是将古代的忠诚、勇敢、道义等“自然的情感保持在第一位的人”,而与之相反的是“社会人”(即“文明人”)。我们应该注意到,卢梭“自然人”观念的提出是有一定启蒙语境的,“自然人”本就是那个时代哲学的公共产物。在《论不平等的起源》的本论中卢梭告诉我们,为了探究社会的基础及其政治性质,当今时代的哲人们提出了“自然状态”及其“自然人”的假设,以此作为研究政治制度或优或劣的参照系数。卢梭是赞成这种分类方法的,但他同时代哲人们对“自然人”假设的表述还差强人意,其结果必然是曲解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及应该追求的完美政治的性质。在卢梭看来,古代人是“自然人”,而当代人是“社会人”,是一种被封建专制制度所腐蚀了的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的理念,《爱弥儿》在这方面必然有思想上的承袭性。自然的状态在卢梭看来是最理想的。他说“:自然让人曾经是多么幸福而善良,而社会却使人变得那么堕落而悲惨。”[6]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在暗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带来人类道德的提高,反而带来普遍的堕落与罪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常早的对“文明”的反思。“社会人”已经被人类社会的种种成规陋习所污染“,回归自然”必然成为卢梭教导爱弥儿的首要原则。那么,如何培养“自然人”,如何“回归自然”呢?卢梭的回答是“: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卢梭为爱弥儿制定了一系列的培养计划,从幼儿时期的爱弥儿到情窦初开的爱弥儿,作者“细数了一生的苦难”[7],相应的采取培养策略,他认为这样才是自然教育应该做的。不难发现,“自然”在《爱弥儿》中显然参杂了“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卢梭本人。卢梭从“社会人”相反的维度去思索“自然人”应然的存在状态,这只能导致主观化的自然。卢梭对自然的理解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较之《爱弥儿》,《庄子》在行文中所言及的“自然”具有不同的内涵。“自然”以纯哲学的姿态出现,显示出形上哲理色彩。以此生发的“自然教育”也显得难以为人所操控。道家处处言及“自然”,“自然”成为得道者的一种处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高于“道”的存在物,“道”也可以说是“自然”的一种概括与描述。道家的“自然”近“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8],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简言之,“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它排除了一切可操控的因素,涵融万有,凌驾于万类之上,产生在万有之前(“象帝之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道家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表述“自然”,这是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以此“自然”观导出的具有教育倾向的“体道”方式就与卢梭的自然教育原则大相径庭。我们注意到,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在论如何教育,他们只是在表述如何以最淳朴的姿态归顺自然。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体察到了靠“自然”来实现自我教化的可行性。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成为道家教化的首要原则———不去向外诉求,而是顺自然发展。那么,到底如何自我育化?《庄子》以“体道”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自育之法。《庄子》的首篇《逍遥游》以“鲲鹏”神话开场,这是暗指了读者直觉思维应该重启,而逻辑思维暂告休假[9]。“游”是一种态度,这是直觉对“道”的体悟,是纯娱乐性、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以“游”的方式来完成对“道”的觉解,这是庄子美育的基本诉求。
游戏的心态本就是童真心灵所具有的基本特点,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宣告瘫痪,审美直觉被唤醒,这本身就是自我育化的自觉追求。庄子中“心斋”“、坐忘”,都是体道的具体途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让人摒除杂念,心境纯一,通明大道,以虚空之心集道于怀,这是入道的关键,也是进入审美之境的起点。在《大宗师》中,庄子还提出了“坐忘”的修心方式,这是对身体感官机能的抛弃,也是对理性思维的扬弃:“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心斋”、“坐忘”是“悟道”的过程,“悟道”的主体是自我而非他人,也即是自我育化。我们发现,这种自然育化的过程是自我的修心活动,我是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主体。庄子没有刻意地去接近“自然”,其美育策略本就自然而然,无须人为的操控。这种哲学范畴的自然教育观与卢梭从政治社会的反面提出的自然教育观是有很大不同的。
卢梭所处的时代是唯理论占据优势的时代,用洛克的著名说法“:我们生而自由,也生而具有理性……年龄带来自由,同时也带来理性。”[10]理性成为了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的助推器。但唯理论的过度发展必然导致独断论,导致另一场思想与文明的危机。在唯理论蓬勃发展之时,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理论模式兴起于法国,卢梭力批理性,推崇感性,显现其不同凡响的哲思。他批判了当时颇为时髦的“用理性去教育孩子”的观念,他说:“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最时髦不过;然而在我看来,他虽然时髦却远远不能说明它可靠;就我来说,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过过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他认为,理性教育不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只能起到负面效用。以此相对,卢梭却对感性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将感性看作人生存的基础与前提。他认为,在人身上“首先成熟的官能就是感官”,然而,“唯独为人们所遗忘,而且最易于为人们所忽略的,也是感官”。他说“: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觉而进入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正如有了这种感性的理解做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说,我们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睛。”由此观之,在那个理性主义占统领地位的时代,卢梭对感官和感性教育的推崇可谓空谷足音,他将感官和感性提到人“存在的本身”与最有意义的生活的高度来认识的确是从未有过的。较之卢梭的美育观,直觉与感性在庄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对“道”本体的体悟本身就非理性逻辑可以达到的,而是靠“体验”,这个过程是对人内在感性能力的一种培养与操练。而且,在《庄子》中,以神话和寓言形式出现的具有隐喻特点的故事俯拾即是,它们以不太连贯的方式串联成文本全部。然而,神话似的场面本就是摒除逻辑理性思维模式的,“以便平息心灵的分析功能同时又唤醒其直觉功能。”[11]
庄子在《逍遥游》一开场就选取“鲲”与“鹏”作为自己理念的寄托物绝非偶然;《齐物论》蝴蝶梦也是借蝴蝶原型(本喻)来阐释“转化”之旨;《人间世》和《大宗师》中畸形的智者,癫狂的哲人都饶有趣味,极富暗示性与启发性;在《至乐》中,“骷髅”意象的运用既表现出庄子看破生死喜乐的豁达,这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可怖意象;《秋水》中的“水”意象,它本身就是中国古典哲学常见的“本喻”体[12],“水”是“道”最恰切的表现形态。隐喻与象征艺术是庄子的文学选择,也是他有意为之的语言设计(“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只有形象思维能力才能较为妥帖地接纳这些有着象征性的哲学启示。这种古老的、埋藏在人类童年期的智慧在阅读《庄子》时被重启,如“童真之心”的复苏一样,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直觉、感性的哲学操练。所以,卢梭与庄子虽用不同的教育策略来达到自然美育的目的,但他们对人感官能力、直觉能力、感性能力都是极为重视的,在“理性”肆意猖獗的当时,他们都力求一种向人类原始情结(感性能力,诗性智慧)的回归。这既是卢梭寻找原始淳朴文明的思想根源,也是庄子对老子哲学艺术化的继承与阐扬.
作者:陈辞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 上一篇:金属商品交易中的互联网安全文化管理范文
- 下一篇:后现代语境下的斯坦贝克研究意义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