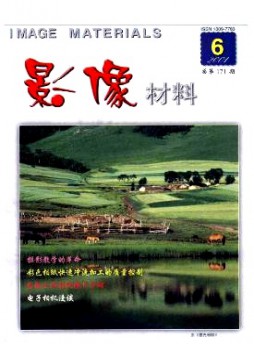影像艺术中的自然主义论文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影像艺术中的自然主义论文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尽管这个团体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整个影像艺术的影响却非常深远。20世纪初,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将摄影的要素归结为三个:距离、中性和简洁。其中“中性”对他来说意即不打扰被拍摄对象,做一个极其安静耐心的旁观者;在技巧上,则表现为拒绝人工光源和修剪底片,追求最自然的效果。埃默森、布列松之后,在摄影方面,又出现了秉承其精神的“直接摄影”、“纯摄影”等流派,而在电影领域,则出现了大量反情节、反主观表达的纪录片与实验影片。影像艺术的主要审美特征之一是“纪实性”,亦即摄影、摄像机拍摄的必须是现实世界中实有的事物(此处暂不讨论后来出现的数字技术对图像的修改与虚构),这一特点往往被视为对影像艺术家的一个重大限制——他们不能像画家或文学家那样天马行空地想像情节、虚构人物、营构现世中不存在的事像。因此,一些影像艺术家为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会试图在生活场景的选择、人物(模特)的典型性、光影的独特性等方面极力彰显个人主观色彩;但另一部分影像艺术家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主观性本已稀少的情形下,索性追求更极端的“客观性”,让“自我”进一步退敛与淡漠直至完全消失在镜头后面,他们放弃对独特生活场景的挑选、对典型人物的突出、对戏剧冲突性的追求,而满足于将自己几乎等同于一架机器,通过胶片漠然的延伸,记录下平凡现实的表面情状和真实细节。维尔托夫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1929年)中,有一个女子早上醒来起床的镜头,她脱去睡衣、完全赤裸,然后穿上正装,再去掬水洗脸……在艺术风气还相当保守、裸体镜头相当稀少的1930年前后,一部生活纪录片中出现这样的片段,颇令人诧异。在通常情况下,一般导演可能都会隐去裸身这一过于暴露的画面、省去洗脸这一过于琐碎的细节,努力展现生活中更有“意味”的场景,但维尔托夫既不回避突兀景象,也不省略细小之事,似乎他只是把摄影机架设在别人的生活里,任由机器自己运转,不增不删,便得到电影。同样在这部影片中,他还拍摄了一个女人分娩及洗浴婴儿的镜头——在那个时候(乃至现在),直接拍摄母亲生产时的身体镜头也是不多见的,这似乎是文明需要避讳的事。所以,维尔托夫的做法极其直率,正如他的信念:“摄影机能去任何地方”,纪实就是无条件的纪实,既无需加入艺术家的主观好恶,也无须避讳文化成规。倘若文学作品以平铺直叙的手段和漫长的篇幅去描绘无情节、无对话乃至无人物的日常景象,多数读者都会弃卷而去。文学史上就出现过这类例证,如巴尔扎克在《幻灭》等小说中对巴黎街道、伏盖公寓的物理景况进行了极其冗长细致的描写,被批评为过分多余的铺叙。但同类电影作品却获得了许多赞同和辩护,似乎影像艺术天生获得了更多的美学宽容,仅仅因其提供了可“看”之物而赢得艺术之域的立足之地。将影像与文学相比较:文学属于“想象艺术”,它呈现给读者的只是抽象的文字符号,读者必须先解读话语符号,然后根据文字意指在头脑中构建出种种想象,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完全没有眼耳等感官方面的直接刺激,总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间接感和不确定性。摄影和电影(电视)则直接提供鲜明具体、栩栩如生的图像,尤其是电影和电视展示的动态影像,对人的视听感官产生更充分强烈的刺激,因此,即便是呈现未经过滤和加工的生活内容,当它们以饱满的色彩和鲜活的动态呈现出来,人们也会产生观看的兴趣。人类的视觉具有强大的“饕餮”欲望,仅仅“看见”事物景象(不需要多么精彩独特)就能唤起人们的浓厚兴致。哪怕是像苏珊•桑塔格所形容的那样:当代过于泛滥的摄影作品已将现实景观贬值为一件件消费品,人们贪婪而迅速地将影像作品“看”掉、消费掉,那种“饕餮视像”的愿望仍然强大,这就是影像作品比文学更能迎合大众口味的原因所在。
从摄影照片到电影、电视,百多年来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作品:“自然主义摄影”的倡导者彼得•亨利•埃默森拍摄的《诺福克的生活与风景》,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名胜区诺福克郡人民的生活和风景为主,拍摄的都是人们生活的日常活动和当地的常见景物,用以证实这些题材也能够成为艺术作品——农夫赶马犁地、主妇院中洗碗、夏日牧羊、秋来割草、干草船航行水面、收工者日暮回家……无一不是寻常人家寻常景象,朴实诚挚地展示了英国乡间生活。以《柏林,一个大城市的交响乐》、《尼斯的景象》等为代表的“城市交响乐”纪录片则都选取某座现代城市,摄下一天之中普罗大众的日常起居活动和城市各个角落的景象。近年来,伊朗导演阿巴斯又对“纪录催生意义”这一理念作了相当极端的探索——如果说前述《柏林》、《带摄影机的人》等作品尚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的话,阿巴斯的电影则对传统审美习惯发起了强力突破:在《十分钟年华老去》中,阿巴斯用整整10分钟将镜头对准一个沉睡的婴儿,婴儿只是睡着,偶尔翻身,最后苏醒,坐起来环顾四周——影片便结束了。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景象到底有什么蕴意?如果一位小说家用长篇文字描述这个过程,读者能接受吗?而阿巴斯向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的影片《五》,则更把“无主角、无情节、无对话”等特征推到极致,全长74分钟的电影,只有五个长镜头:(1)海滩上一截漂木被海浪卷裹着来回地翻滚;(2)海边来来往往的过路人;(3)海边几只狗静卧和嬉戏;(4)沙滩上一群鸭子从左跑向右,然后又折回;(5)夜晚水边的月影蛙声,继而电闪雷鸣,雨点纷落,最后鸡鸣、天亮。这部电影挑战了许多人的观念与耐心,观众们难以理解这种毫无情节、镜头之间也没有关联的电影。而在阿巴斯看来,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位导演都不会比日常生活本身更具影响力,因此他认为电影要做的事就是努力接近生活,并尽量抽离自己的主观情感。在他的电影中,世界不再被人驾驭和安排,相反人只是世界的偶然闯入者,“生活才是电影的主角,电影就好像只是给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加一个景框”。
二、自然主义影像作品的文化功能
从埃默森的照片到阿巴斯的《五》,许多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影像作品得到了多数理论家和观众的喜爱和承认,究其原因,其积极意义或可归结为如下几方面:首先,正如英国学者约翰•伯格认为的,摄影是迄今为止最能逼真记录现实的艺术,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艺术能比摄影更精确、细致、忠实地反映自然。影像技术“拯救了不保存起来就会被磨灭的外貌,将它们不变地保留下来。事实上在相机发明之前,除了人类的心灵所具有记忆能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有这种能耐。”但人的记忆通常与情感相关,受到越强烈刺激的事件记忆越深刻,而日常琐事则容易淡忘或误记(甚而由于精神创痛、自恋自欺等原因而扭曲记忆)。有了影像纪录之后,所有社会历史或个体生命的迹象都有可能被完整准确地保留下来,供人们重新品味和挖掘意蕴。正如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对电影的赞言:“多亏电影的贪婪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们才得以看到记录在胶片上的本世纪洋洋大观的现实生活风貌。……电影胶片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各种物象,连无足轻重的偶然发生的细微末节亦出现在银幕上,以求生存权力。”
许多纪录片都保留、“拯救”了这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影像艺术,人类才具备真实确切地记录诸种生活细节的能力,同时也开始比从前更关注细微、边缘、非主流等生活现象。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对此深为赞赏,他认为细小、边缘之物其实也对现实生活产生着潜在而深沉的影响,尤其对普罗大众来说,震动社会的英雄人物或重大事件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往往已是余波将尽,大众的生活本来就是由琐碎细小的事物搭建起来的。影像艺术能够以直接手法捕捉现代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无法用即存框架去套的东西”,因此本雅明希望电影发挥其快捷准确的记录专长,去捕捉那些对人们产生潜在影响却又常被忽视遗忘的东西,催促人们去注视和反思生活中默然却又决然地影响了现实走向的东西。进一步来看,自然主义影像艺术在美学上的另一种启示,在于某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传统艺术创造过程的“先发现、再创作”的常规顺序,呈现为一种“先纪录,后赋意”的过程。换言之,通常大多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先去经历、发现生活中“有意味”的东西,觉得有必要以艺术形式保留、彰扬,便以作品描述表现之;自然主义影像却可能是先忠实摄下生活片段,然后再去挖掘、追寻其可能具有的意味。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张以庆在谈到其影片制作时透露,他每次拍片,摄下的素材带都远远超过最后成片的长度(例如长50分钟的《舟舟的世界》是从2100分钟的素材带中剪辑出来的),很多时候,他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能拍到什么,只是先摄下眼前人物的生活,事后再去追寻、提炼其意味。张以庆说,纪录长片《幼儿园》剪辑完成后,他的摄影师看到经由导演提炼浓缩过的成品时“非常惊讶,因为他开始不知道他拍的东西能做成什么。当时我们……都带有很大的无意识”②。类似的经验,在其他纪录片导演的创作中也常常出现。影像摄录的某种魔力在于: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一旦进入摄像机,化为影像在银幕上展示出来,就会催促甚至强迫观众去品味这些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了的生活,并常常意外地发现一些当时未曾意识到的意趣——某个身姿表情意味深长,某句话语听来似有潜台词,一些器具或环境似乎具隐喻意味……电影将被忽视的日常生活以“陌生化”的方式重新展示给人们,激活我们钝化的感官;也只有当这些平凡景象呈现在银幕上,获得一个艺术“场域”时,人们才开始重新以审视的眼光去注视它们。影片“强迫”人们去凝视和品味日常生活,鉴赏和分析这些习见景象;而日常景象呈现为影像后都或多或少显得意味深长起来,仿佛成了同类物质、同类生活的代表或隐喻。如前苏联“电影眼睛派”所相信的:艺术家赋予事物“奇特崭新的面貌,自由而富有创造激情地化腐朽为神奇。”藉此,个人或社会的历史可以得到更详尽细密的体悟与评价,甚而能发掘出原本可能被忽略或扭曲的重大意义。
再深入探究,自然主义影像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史鉴意义:为现代生活、地域文明留下人类学的记录和见证。伊芙特•皮洛对此作了较好的论述:“这么多习见的景象有助于对一种新文明做出判断。……电影使我们了解新的人类学,电影能够记录下一些新现象,记录下当代千变万化的习俗。它记录下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面貌。它以‘魔力般的精确性’捕捉到尚无定称的形貌、身姿手势和行为模式。电影仿佛翻阅一页又一页硕大无朋的照片小说,慷慨大度地把一切财富掷于我们面前(除了它无能为力的文学描述和科学分类),使我们目睹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人之间不断变化的新关系。”德国电影“新客观派”则认为:纪实影像直接对当代文明世界进行写实,“使人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找到现代艺术与记录材料:那就是事件。它们既不是通过新事物的刺激,也不是通过具有异国风情背景的高尚野蛮人的浪漫主义而给人留以印象的。”这类影像具有某种存在范型或原型情境的意义,因为这“无数琐细的表象”将汇流为一个宽阔的潮流,最终昭示出“日常生活的客观流程”,即支配现实生活行进的静默而强大的力量。这种力不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或革命运动等宏大巨力,而是贯穿在普罗大众日日夜夜最根本的行居衣食、一饮一啄中那种决定基本生存的沉静绵长之力,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凝重坚韧的存在之力——即如海德格尔从梵高的《农鞋》中体验到的诗意哲理一样——大多数自然主义影像作品展现的就是这一层面的存在意义,现世生活就在这类景象日复一日的叠现与行进中缓慢、坚定地流淌。电影使这类景象具有了某种存在范型或原型情境的意味,催促我们从人类学视角去观照现代生活,对此时此地的文明获得了解和判断。简言之,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纪实影像“要用社会存在的事实演绎一个过程,记录一种文化”,“于日常礼仪中找到一个社会的民族精神,理解人类是怎样想象世界之秩序的。”从海德格尔到本雅明、伊芙特•皮洛等理论家对微观、日常景象的重视,也体现了自精神分析学、现象学、新历史主义思潮以来现代性美学的一种趋势:从具体、直观的鲜活事物入手观察世界,向主流、常规意识的边缘处寻找意义,让原本沉默的事物说话,使曾被排斥在艺术视野外的日常生活得以呈现并具有历史意义。因此,从20世纪早期至今的许多电影自觉展开了这样的美学追求,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以其对现实的真切记录帮助人们理解现代世界、寻获生命意义。
作者:钟丽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 上一篇:缅甸岁月中的自然主义论文范文
- 下一篇:野性的呼唤的自然主义论文范文
扩展阅读
- 1脑脓肿影像学
- 2转换影像压缩
- 3影像技艺的思辨研究
- 4医学影像存档
- 5医学影像存档
- 6听皮层的PET影像学研讨
- 7骨折的影像学辨别判别
- 8龟影像学和血液学
- 9胸部外伤影像学诊断
- 10骨膜骨肉瘤影像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