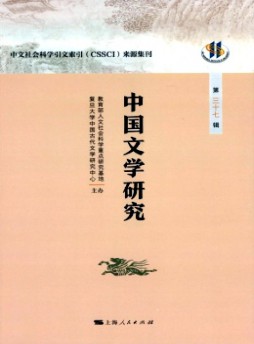中国文学趣味探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中国文学趣味探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文学趣味是审美主体在文学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倾向性,对某些审美对象或对象的某些方面的特有的喜好和偏爱。”审美主体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不同,生理气质和性格爱好的差异,使得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各有所偏好,不可能等同划一。”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之类鸿篇巨著的欣赏,对短小凝炼的作品如泰戈尔的《飞鸟集》等抒情诗的欣赏;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作品,欣赏者眼光都是不同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渐进产生的,是人通过社会实践产生的一种审美能力。年龄较大的人,受传统教育较深,他们长期受古诗词的熏陶,必然更喜欢格律诗、古典戏曲,他们觉得这类作品的韵昧悠长,意境深远,正是悠长深远的文学趣味。年纪较轻的人则对此类作品没有那么感兴趣,他们更多地接触了西方文学,对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朦胧诗才够味,才能传达他们的心声,青年一代对文学趣味的发掘是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产生的现代意识相联系的。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尽管人们趣味各异,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欣赏和审美趣味还是可以被引导改变。文学评论家不停留在个人的兴趣爱好上,将自己的审美趣味摒除,对审美客体进行公正的判断,以引导广大读者进入更高的审美层次,获得更多的高雅趣味为责任。因此,文学的审美趣味在引导下也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区别于一般读者的评论家们,必须在对作家及其作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审美理想来解释作品,使作品获得升华,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非自觉的东西变成自觉的东西,即原来作家未意识到或未充分意识到的东西上升为自觉的充分意识到的东西,这时评论家完成了艺术再创造的任务,也将趣味深入发掘出来,渗入欣赏者心中。对于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的欣赏,历代诗评家褒贬不一。近代诗评家认为这首诗是诗人运用典型化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认为前两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写了江南春明媚的一面,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特意把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明朗与朦胧相映衬,就使得这幅“江南春”图画更美丽、更富有层次了。一般读者欣赏到此,一般的审美趣味似乎已经把握在手了,而精心的诗评家们却别开生面,以自己审美理想的光束照射这首绝句,发现了诗的异彩。认为后两句是对南朝统治者一面向人民无穷榨取、一面疯狂佞佛的冷嘲,问“至今还剩下多少掩映于烟雨之中?”又说:“历朝的封建统治者都逃不了覆亡的命运;然而,千里莺啼,红绿相映,江山依旧健在。水村山郭,酒旗摇风,人民也依旧顽强地生活下去。诗题叫作《江南春绝句》,也值得我们寻味。”[1]这就是升华的结晶:江南春的“春”真正内涵是:江山永在,人民永在,反动统治者必朽!这种理解中透露出欣赏者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是欣赏者的理想信念在诗中找到了回响,于是欣赏者就借诗发挥了。这就是评论家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再把自己的独特的审美理想投放到作品中去,从而使作品的境界获得升华,发掘出一些作家本人未必自觉意识到的审美趣味,这正是评论家对趣味引导的责任所在。引导者用自己的审美理想照亮作品,升华作品;在审美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反思,并把新获得的更高层次的审美理想投放到已有的审美理想中去,使自己的审美理想得到新的组合和升华。引导者在对一般趣味的理解不满足中不断地进行调整、组合、升华,才会使自己的审美理想不断地飞升,越来越接近于艺术的圣境,才能让读者群接受趣味的异彩,获得趣味的理想境界。
一、自然之趣的再现
趣味是艺术的本质和作用[2],是艺术的灵魂。梁启超曾经说,文学、音乐和美术是专门从事磨砺感觉器官以诱发趣味机缘、增强生命趣味的三种利器。又将审美趣味产生的源泉归结为三派,其中一派就是描写自然之美。自然之趣的发微正是源于艺术的本质与作用。艺术因最能导人游于理想而予人趣味,对日常内在心理和微妙情感生动的表现是艺术给我们自然趣味的深刻根源之一。日常习见的事,现实生活中体验的喜、怒、哀、乐等心态,活跃在纸上,惟妙惟肖,拨动读者的心弦,使读者把心的微妙之门打开获得愉快。这其实就是由情感宣泄、心理共鸣而引发的畅快,称之为“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对现在环境不满,是人类普遍心理。肉体上的生活即使被现实环境所捆绑,精神却渴望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以享受自由的快乐。“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我们欲求趣味,这又是一条路。”[3]艺术中有不写现实而纯凭理想构造的,而且艺术所构的理想境界形形色色、优美高尚、富有魔力,能引导读者跟着它闯进一个超越的自由天地。另外艺术给人以再现自然的趣味。欣赏自然之美,领略出水流花放、云卷月明等美境,就“可以把一天的疲劳忽然恢复,把多少时的烦恼丢在九霄云外”。若把美境印在脑里头,令它不时复现,也同样令人心爽神畅,这种“对境之赏会与复现”,是艺术唤起人自然之趣、世界赋予人类自然之趣的一种重要方式。[4]人与自然之间有着近似本能的情感关系,这种本源性的和谐使得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在自然中感到欢欣舒畅。人类不管从事哪种卑下的职业,身处于多亩烦劳的境界,总有机会和自然之美相接触。这就是说,我们不必整天闲游于山水名胜,为与自然接触做专程的旅游观光,就在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行程中,随时都可能得着亲近自然的机会,而对自然之趣的欣赏,文学便是一种很好的媒介。只要心存天然之趣,善于随处捡拾自然之趣,逢春便是春。梁启超对于自然之趣的捕捉尤为突出。他在气势雄壮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的太平洋途中,情激昂、神飞扬,乐观精进地欣赏着“海云极目何茫茫”、“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的太平洋壮景。在为发起倒袁运动而匿踪南下的冒险途中,梁启超竟将偷渡当作清游,在《从军日记》中写道:“余起,张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盖我生所未见也。”一战后赴欧考察航海南洋时,梁启超更是随时享受着与自然富有灵性的亲和交融,“在舟中日日和那无限的空际相对,几片白云,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来由和去处。晚上满天的星,在极静的境界里头,兀自不歇的闪动。天风海涛,奏那微妙的音乐,侑我清睡。”[5]文学自然之趣是在文学审美活动中敏锐观察体验,发自于本心的对自然的热爱。抓住俗务奔趋中遭遇幽奇山水的时空境遇,在辛苦劳顿中也能随时随地享受人生佳趣。既不是不得志时的寄情山水,也不是不问世事的高蹈世外,而是出于他对人生遭际的事物、对人生到场之事物浓厚的兴趣,出于随处俯拾生命佳趣的天真烂漫情怀,出于对自然万象的生动性、丰富性、淳朴性的天然喜爱。自然之趣的趣味论张扬的艺术人生并不表现为对现实和功利的纯粹超越和解脱,而恰恰是对生活的热情投入、对生活的迷恋和拥抱。自然无所为的生活状态是为了更自由更愉悦更有兴趣地去从事必然内含功利性的生存活动,从而进入自由创进因而活出乐趣的乐生境界。在文学活动的审美中,趣味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既空灵且充实的和谐生活,才是真正现实的自然之趣。
二、高雅情趣的提升
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又有高等和下等趣味的分别”。[6]所谓高等趣味就是审美趣味。文学艺术的本质作用就在于以审美趣味来恢复人的审美本能,以维持和增进人的生活健康。从艺术表现上看,重视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作品才能给人以高雅的审美情趣。高雅情趣的提升在文学作品中尤其体现在戏剧文学的艺术表现上。在各种艺术里,一部作品由受欢迎以至被遗弃,其变迁之急剧,恐怕也没有甚于戏剧的。戏剧作品凭借着某一时期技术性的发展给观众以递进的时代刺激和快感,作品主题不够深刻也会经不起时间的淘汰。要使一部戏历久不衰,那就“必须使作品先成为文学”,归根到底,戏剧的文学性是重中之重。看好的剧本在舞台上作有效的表演,那才是最理想的事。“剧本的写作是创造,演员的艺术是再创造”。高雅情趣的不断提升就要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完成。要培养高尚的趣味,发挥善的美的情趣,压伏、淘汰和铲除低级的、丑恶的情趣,推动人类的进步,趣味教育最好的工具就是艺术。早期新月派热衷于文艺美的探讨和交流,梁实秋认为“戏剧艺术是最高的艺术”,鉴赏戏剧“需要有极深的想象力”。他对“剧本第一”的坚持,实际上就是对戏剧文学艺术性第一的坚持。深邃的理解人生,通过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宣扬,表达了高雅的审美情趣。剧场的舞台艺术与题材结构的文本艺术,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古希腊戏剧之所以取得成就,原因之一在于观众品位高,歌德戏剧作品排演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观众。一部伟大的作品并不是只供少数人鉴赏,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供大多数人提升高雅趣味的目的。戏剧作为诗化的艺术形式,前途的关键在诗人的掌握里,也在观众的理解里。“我们不必着急、不必心焦,只需静心的等着,好像漫漫的长夜里我们等着天明一般的等着真正戏剧诗人的出现”,在文学审美的过程中,期待观众高雅趣味的提升。高雅情趣并不是和高高在上、奢侈享乐、脱离社会实际等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雅的情趣在左翼文艺中被泛化为贵族化的审美倾向,一直是诟诬的重点,无论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还是建国后的无产阶级文学,由于阶级观念的过分强调,贵族化的审美倾向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唾弃的对象。而对于高雅审美趣味的积极意义,我们的认识显然不够充分。这种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讲求内容充实、格调清新的艺术化的超越性美学精神,是克服非文学化倾向的关键因素,不仅对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简单化、模式化是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有效地抵制了文学的庸俗化和粗鄙化。文学的贵族化标榜文学艺术的纯正性和艺术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贵族化不是一个与平民化相对立的概念,而是是一种自觉的、反映社会的高雅审美趣味的美学追求,是多种文艺美学中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审美意识中高雅趣味的认同,必然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品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也正是以戏剧文学为例探讨高雅趣味审美倾向的最终目的。
三、悲趣传统的形成
悲观主义思想观念在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庄子对人生如梦的感叹,对不合理现实社会的厌弃与退避早已成为传统诗文吟咏的主题。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庄子的悲观主义哲学对现实人生、对人的生存境遇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知北游》),充溢着对生命的偶然性、有限性以及人生终日劳苦而意义何在的悲哀与困惑。在《德充符》、《人间世》、《知北游》中更有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悲剧性的觉悟“人之生也,与忧惧生”。他竭力用齐万物、一死生的“天人合一”观念来弥合这种深沉的悲剧感,用“心斋”“坐忘”实现对人生悲剧现实的审美超越,金圣叹的以审美求解脱思想可以说正是庄子以“忘”为标志的审美超越精神在戏曲批评领域内的回应与承续。佛家的色空观进入文艺领域后在客观上对写实的创作精神起到了推动作用,弥补了庄子的“忘”对人生悲剧现实的回避。无论是肯定欲望亦或是放纵欲望以达到对世俗礼教的反抗,为文人带来的均是无法排解的痛苦。因此,欲望、痛苦与解脱逐渐成为文艺审美观照的对象,人生境遇、生命本质等人生根本问题也日益成为文人思索的时代问题。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在中国文学领域内的形成是时代社会政治与各个时代文艺思潮共同作用的一个过程,在戏曲领域中以悲为趣的传统是中国文学以悲为趣传统的缩照。“先秦悲哀原则,类比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诗学。两者都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7]悲乐并传也像《淮南鸿烈》、《声无哀乐论》这些相关的美学著作所论,可以看作是在音乐客体本身不变的情况下,由欣赏主体自身的情感波动来比附或想象客体的相应存在状态。元代曲学家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对十七宫调中与悲怨有关的调性也作了论列:“南吕宫感叹伤悲正宫惆怅雄壮”“,商角悲伤宛转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等,从音韵上对悲进行了明确的总结。作为基本存在方式,悲哀原则以时间、空间和一定的度量,形成悲而有时、有地和有节的外部规定性。其内在根源乃是主体人格情感三大依据,即由人生的悲哀导致恻隐之心的形成,由道德的悲哀导致是非羞恶感的形成,由理想的悲哀导致浩然之气的养护。[8]明代后期社会的黑暗与动荡现实对文人生存境遇以及文化心理带来了巨大威胁与悲观幻灭感,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悲苦的情绪在文艺领域内蔓延,个性解放和独抒性灵造就了中晚明文人的狂狷与放荡。人们在关注人尤其是个体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与传统、世俗的激烈对抗所造成的心灵分裂与痛苦。这种痛苦在戏曲创作中的表现,自汤显祖开始至清初南北孔创作中悲观主义倾向的日趋增强,而诗文领域内,从公安派提倡性灵到竟陵派渐渐转向苍凉、孤峭的艺术风格同样体现出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渗透并渐占主流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艺思潮的浸染下,悲观主义向戏曲批评领域内渗透也就不足为奇了。悲剧中审美快感的获得,并非单纯因为善恶有报的因果论,以悲为趣还在于悲剧角色的相互转换。广为人知的戏曲人物陈世美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角色,无论是从人生痛苦本质的认识上,还是对人的欲望与解脱的关注上,其高中状元到最终彻底的追悔,个人结局的转换,“终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钟,发人深省。”
传统的文艺批评主要集中在作品的风教、载道等社会政治功用方面,即使追求纯粹审美境界的意境论等也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物我合一,神与境合等情景关系上。中国的文艺创作观念继承了审美超越等观念。悲剧在从人本出发,通过文艺来对人生本质和存在价值的探寻中,追问人生痛苦的根源。可以说,没有这种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对戏曲批评的介入,对中国文学的介入,就没有悲观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融入。古典悲剧思想的形成和古代悲剧性文学杰作的诞生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