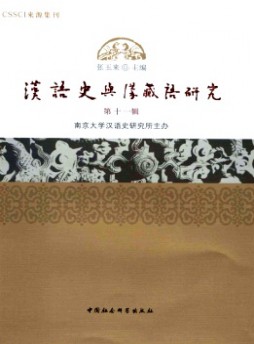汉语语法学史分期的重构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汉语语法学史分期的重构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著名精神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层,分别处在人心理的深层、中层和表层。实际上,当人们与某事物产生联系却未感知时处于潜意识状态;当人们明确感知到事物存在并有意去判断、辨别时处于意识状态;而当人们朦胧感觉到其存在却对其不能作肯定判断时,就处在前意识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对某事物的认知及由之引发的行为都可以看作各层次意识之间的竞争或博弈。以下从人对事物的意识逐层递进关系来分析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
(一)潜意识本能流露期(先秦—1323年)
从先秦时期具有语法分析资料的《墨经》开始,一直到1323年元代卢以纬虚词专著《语助辞》出版前的这段漫长历史中,人们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处在本能反映状态,完全是一种兵来将挡的架势。但“今人用现论、方法分析出的语法现象,或是从语言事实中概括出的现论、方法,古人有所感性认识,以具体的分析事实表现出来”[1](着重号由笔者添加)。各种语法现象及语法规则已然潜在呈现给人们,但人们并未觉察;在讲经论道注书时,遇到解释一些遣词造句的规则,无意中就流露出语法分析。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语法意识应该不具备,但各语法要素(词、词组、句子)、语法研究方法、语义关系均有所涉猎。如:(1)《经》名:达、类、私。《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俪。将名词分为抽象名词、个体名词和专有名词三类。(2)《墨子•经上》:“谓:命、举、加。”《墨子•经说上》:“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暗指出汉语的三种基本句式:“名—名”主谓判断句、“名—动”主谓表述关系的叙述句和“动—名”述宾关系的非主谓句。(3)“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谷梁传•桓公二年》)。词句似在分析汉语语法中的虚词和语序,实际却是展示当时的社会尊卑有序观念。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南宋陈骙的《文则》。《文则》堪称我国第一本语法修辞专书。全书主要讲经、子等书的修辞句法问题。相比之前著作语法观念的零星、琐碎,《文则》则是对以前资料的概括性总结,从宏观层面抽象理性地总结了助辞的作用、类别和句法。但陈氏也仅流露出一丝语法意识,如说助辞作用是理清文路,指出倒装现象等;从众多实例中归纳出一些句法规则,如“先总而后数”、“先数而后总”、“先总之而后复总”等,实为当今复句、多重复句和句组结构关系的分析。现人对当今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关系和句型句式均有涉及,还出现了“句法”、“语法”、“语病”、“实字”、“虚字”、“死字”、“活字”等语法术语;但无论是对词、词的组合、句式的分析,还是对语法术语的运用,古人都只是机械地、下意识地进行,并未意识到汉语语法的存在;而且,对语句的分析分散于一章一句,只是古人讲经道义时的一种陪衬、一种附带;也就是说,“这些书不是径直的对语句作语法分析,而是各书的论述中表现出了语法分析,也可以说是从各书的论说中我们发现其中蕴含有语法分析。”[2]
(二)朦胧欲试、初露锋芒期(1324—1897年)
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语法特色。古代对虚词的专门研究者不少。从元泰定元年(1324年)出现了卢以纬的虚词专著《助语辞》(原称《语助》)到清代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前的五百多年里,语法学者对虚词的研究可谓入木三分。专著数量不少①,且著述随着时日推移而日渐深刻、准确、丰富;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著作除《语助辞》外,还有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三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词专著是对前人约两千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尽管深受词义训诂影响,但又不同程度地摆脱其束缚;它们不仅阐释虚词意义,更偏重分析句法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统置、句式特点等,意即这些书不是所谓的“虚词字典”,而是一本语法书,只不过研究对象只是虚词罢了。当然,这些作者仍没明确意识到“语法”存在,只是朦胧感觉到分析词义外,还要结合语言事实分析其用法。这较前一阶段是有进步的。如:(4)毋(《助语辞》)。禁止之词。韵书云“女”中加一直,禁其勿为奸邪之意。又“无”字与之通用。……诸书中又“亡”与“无”通,只是俗语“没”字。其有“毋亦”、“无亦”、“毋乃”、“无乃”、“毋宁”、“无宁”之类,此“毋”字,却是带“莫”字之意。(5)以(《助字辨略》)。《左传•昭公十三年》:“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杜注云:“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愚按:“鲁故之以”,犹言以鲁之故,倒文也。(6)者(《经传释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或字者,或言也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曰:“王氏(指王引之)在对虚词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对一些虚词的语法作用及语法意义作了详尽的描述。”除大量虚词专著外,这一时期的常规性语法知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运用于蒙学的语法教材《对类》和“文法”术语,这说明此时古人多依据文法(句法)构造作训诂考据,较之前一阶段,此时是有一定朦胧意识地观察句子的结构规则以及辨认句子结构规则运用的正误。划分词类能依据词在句中的位置和词义特征,还对句法结构、句法语义关系、语法分析方法、古汉语特殊句式等进行了阐释,甚至还能结合语用因素考虑语法知识。如:(7)“茸,草茸茸貌。”盖草初生之状之茸,“鹿茸”盖取此义。……形容之词,单音与重言同(《说文句读》卷二)。(8)“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念孙按:“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读书杂志•淮南子•人间•良马》)。(9)“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犹“于”也,此倒句也,“何世于起”犹言起于何世也。……安、于一声之转,故“于”字或通作“安”(《经义述闻•大戴下•何世安起》)。
(三)自我能动表现期(1898—今)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它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开辟了中国语法学的第一块里程碑;继它之后,汉语语法著作犹如雨后春笋般冲土而出。从1898年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历程既充满荆棘坎坷,又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与值得思索的韵味。范晓先生说:“20世纪中国的语法研究,主要是中国学者向国外的各种语法学说学习和借鉴。”[3]的确如此,尽管中国语法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汉语语法学的存在,但由于语法理论的缺乏和历史因袭的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语法学者多是用国外语法理论的外衣套用在汉语语法现象上。当然,在借鉴基础上,我国语法学者最终认识到汉语语法的特殊性,并能对外国理论兼蓄并收、合理运用,将汉语语法学推向更深一程。依据这一阶段语法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特点,分为两个小阶段。
1.假借参考寻求自我期(1898—1966年)。语法学者们习惯于把《马氏文通》到1938年的“文法革新”称作语法学的“模仿时期”,“看来似乎可以作出定论,其实不然。首先,应该肯定《马氏文通》是参照了西洋的‘葛朗玛’,《新著国语文法》也确有仿照英语语法之处,但这是学术交流的正常现象……其次,两部著作都存在符合汉语特点的创造,例如都放弃了西洋语法的形态部分,都注重句法。”[4]而《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者清醒意识状态下的产物,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系统语法著作依靠的情况下,借鉴拉丁语法是可理解的,何况马氏并非事无巨细均依拉丁,“也继承了一部分旧有的说法”[5]和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助词”一说);所以说,《马氏文通》一书及此后一直到1966年这段时间里产的语法著作都只能说是在阐释汉语语法自身特点和创立汉语语法自身体系的意识下,采用了假借、参考国外语法理论的手段。这一时期,无论古汉语语法著作还是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数量都是可观的。其中,不乏参考西方传统语法的语法著作,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暂拟系统”和苏联语言学;也有运用美国结构主义理论确定语法观点和创作语法著作的,如陈望道依据“功能”,从配置(组合关系)求会同(聚合关系)来决定词类;方光焘的“广义形态说”、陆志伟的“同形替代原则”;以及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胡附、文炼主张用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区分词类,熙的《说“的”》和《句法结构》,等等。不可否认,假借参考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寻求自我汉语语法的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汉语的词类问题》(一)、(二)和吕冀平著的《汉语的主宾语问题》,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以及主宾语的判断问题提出了符合汉语特点的见解。
2.审视批判、追求至善期(1978—今)。这一时期,汉语学家从单纯模仿西方语法理论走向自主总结汉语语法现象和挖掘汉语语法规律,从而尽力摆脱模仿、寻找自身的研究路径。这一阶段的语法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最大的亮点是出现了一批自觉整理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如果说假借参考努力寻求自我阶段仍是在西方语法理论影响下的追求之作的话,而林玉山1983年发表的《汉语语法学史》就正式开启了汉语语法学者清醒意识并研究汉语语法学的大门。它“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到当代、系统而又完备的汉语语法学史,起了某种奠基性的作用”[6],是名符其实的“汉语语法学史的奠基石”[7];大门开启,原先被禁锢于门内的语法学者们蜂涌而出,接着出现了一批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分别是马松亭的《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1997年修订本改名为《中国语法学史》)、董杰锋的《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和《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年)》(商务印书馆,2011)。这些语法学史学者均按照汉语语法学本身发展脉络,对汉语语法学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邵敬敏最具代表性。他分为酝酿期(西周—1898年)、草创时期(1898—1936年)、探索时期(1936—1949年)、发展时期(1949—1978年)、创新时期(1978—今)。
其次,选择引进的西方语法理论必须契合汉语本身语法规律。寻求自我特色,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敞开胸怀,在吸收鉴别中发现自身规律与特色。故在这一阶段,汉语界针对汉语重语义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西方的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和俄罗斯的语义学派。代表作有:戴浩一、薛凤生主编的《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搜集了《汉语使成式的语义》、《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与汉语句法》等13篇论文,多是从功能语法观探讨汉语特殊句式和特殊语序;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沈家煊的《不对称与标记论》和《“有界”与“无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诞生及其影响》、《汉语语法的类型学视野》等;张家骅等著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等等。在探索汉语语法现象和总结汉语语法规律时,学者们以西方理论作为理论基石或阐述起点。
最后,加强寻求汉语语法本身特色。与西方语言通过形体变化来表达各种语义不同,汉语语义是由大量虚词和语序变换来实现的,这就导致了汉语语法学者从两个角度探讨汉语特色:第一是语形角度;第二是语义角度。此时期纯粹从语形,即形式语法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数量极其有限,主要体现在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近代汉语指代词》上;在同时,学者们意识到语言形式的形成是一个逐渐演变过程,故多从历史语法角度探讨汉语语法特色,有洪波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吴福祥的《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和柳士镇的《汉语历史语法散论》等。相反,着重从语义角度探讨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的著作则日渐增多,典型代表是李葆嘉和徐通锵,二人旗帜鲜明地指出汉语就是一种语义型语言,语义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是所有语言的出发点与归宿。李氏先后发表的《汉语起源于演化模式研究》、《语义语法学导论:基于汉语个性与语言共性的建构》和《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徐氏发表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和《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都强调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区别,并初步提出了汉语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汉语语法学要以一门学科的身份立于诸学科之列,必须要经历汉语语法学者对其由潜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显意识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转变过程又恰恰构成了汉语语法学史。所以,汉语语法学史的酝酿、产生和发展过程实际就是语法学者逐渐认知的过程。(本文作者:冯雪燕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 上一篇:关爱女孩纪念宣传活动通知范文
- 下一篇:地方政务公开工作方案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