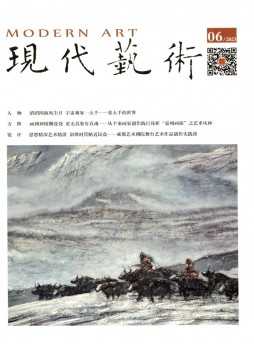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写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多重身份的形塑
(一)现代文学批评系统的建构者近代以降,众多青年才俊远赴欧美,寻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良方,但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异域思潮时却有了不同的抉择,胡先骕就为新人文主义学说所折服。这派学者延续了新古典主义者的思考,鄙夷科技发展与物质层积带来的现代文明病,主张以“人的法则”取代“物的法则”,他们揭批了培根、卢梭崇奉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试图以新伦理、新观念重建人心与世界,而“最精于为人之正道”的东西方贤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释迦以及孔子成为其效法对象,“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4]胡先骕曾亲炙受教于著名学者白璧德,回国后则与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梁实秋等开启了新人文主义的东传之路,将其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新文化的重构之中,并因此与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派形成了对立的话语攻讦态势。文学革命派认同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进化论,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后来的必然比先在的进步,“新”等同于“有价值”,“旧”则意味着“价值”已然散失。如此,兼具时空特性的文学就被简化了,成为单一的时间序列产物。胡先骕并不否认进化论,也不反对科学思维,但对进化论者秉持的线性思维和历史发展遵循某种绝对秩序的理念缺乏信心,反驳其无法解决精神问题,进而指责胡适等“滥用了进化天演之名”,生吞活剥地将西方社会学概念平移到文学领域。可见,尽管文学革命派与胡先骕均以西学为祈向,但由于西学取径上的差异,以及各自本持的文化“前结构”,形成了一种反向的叙述向度。在文化姿态上,文学革命派批评体现为一种西方理论的强势同化,胡先骕的批评则是将外部质素置入自身的批评机制中,进行有限度的调适与阐发。文学革命派强调启蒙,侧重文学的工具性,虽然也不忘指明文学性或独立价值,但却被社会思潮裹挟而显得乏力。胡先骕则认同带有反思启蒙特征的观念,关注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的自律性,重视文学的普遍价值:非实用性。种种差异就造成了他们在关于书写语言的使用,以及对各种文学思潮的评鉴等方面的歧义纷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胡先骕等就被当作新文学建构的破坏性力量,即便是相对中立的研究者也总是以文学革命派天然正统正确的立场进行审视。而在文学革命派建构的现代文学批评评判体系中,他们将自己塑造成有力的、建设性的部分,其他对立的个人、团体就被抛到了“他者”的网络中,“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5]胡先骕以及“学衡派”其他成员的际遇也大抵如此,后来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对他们作了遮蔽式的叙述,即便是种种合理因素也被弃如敝屣。但如拉塞尔•柯克所言:“新人文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场以攫取国家权力为意图的政治运动,它是一次复兴人们的思想和良知的努力。”[6]深谙新人文主义思想神髓的胡先骕力图以文学批评的匡正力量恢复人们对审美以及道德的感悟,这就无形中对占主流的文学革命派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了纠偏作用,故有学者称“胡先骕是五四新文学革命派的诤友”[7]。到了30年代,茅盾批判写实主义陷入无主题的价值判断,得了“丰肉弱灵”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胡先骕文学忧虑的一种间接回应。因此,单纯从进步、落后的表层认知来辨析、判断他们之间的争论显然是不合理的,纠结于新与旧、进步与反动,忽视复杂性的研究无法真正地解决文学问题。无疑,文学革命派建构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样态,胡先骕们则参与塑造了与之相对立,却具有补附意义的别样叙述,大致可称作现代文学批评的新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倾向。如果将现代文学批评视作一个多元系统,文学革命派批评家与胡先骕们的批评则是这个大系统下的两个子系统,他们之间其实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复杂关系。自然,只有将他们各自侧重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启蒙与审美等认知、观念兼融一处,才可算作现代文学批评的完整构成。
(二)文学批评规范的策制者胡先骕对文学批评本身也有明确的学科自觉意识,他试图通过对批评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与规范为文学批评提供一种科学的精神及合理的方法,并响亮地提出“吾人之责任,在创立批评之学”[8]。胡先骕对当时评论界极其不满,认为过多“伪妄与恶意之批评”导致了“固有文化徒受无妄之攻击,欧西文化仅得畸形之呈露,既不足纠正我国学术之短,尤不能输入他国学术之长,且使多数青年有用之心力趋于歧途”。因此,他力主规范批评者的责任,并总结了六点要求:1、批评之道德。“批评家之责任,为指导一般社会,对于各种艺术之产品,人生之环境,社会政治历史之事迹,均加以正确之判断,以期臻于至善至美之域,故立言首贵立诚,凡违心过情好奇立异之论,逢迎社会博取声誉之言,皆在所避忌者。”2、博学。“须于古今政治历史社会风俗以及多数作者之著作,咸加于博大精深之研究,再以锐利之眼光,为综合分析之观察,夫然后言必有据,而不至徒逞臆说,或摭拾浮词也。”3、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不“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4、有历史的眼光,“不宜就一时一地一党一派之主观立论,必具伟大洞彻之目光,遍察国民性历史政治宗教之历程,为客观的评价,斯能公允得当。”5、取上达之宗旨。6、勿谩骂。“他人之议论之或不当也,仅可据论理以折之,且彼与我持异议者,未必全无学问全无见解全无道德也。即彼论或有未当,亦无庸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而只有坚守这些标准,才能产生中国的“圣钵夫、勃兰德士、白璧德”。[8]其实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也对批评主体的素养作过要求,惜均为零碎的散论,并且他们认同智慧和见解本身的质量固然紧要,而某一见解是否尖锐、明快,是否有排他性和独特性才是关键,所以他们往往高扬主体意识,以至于在摧毁某种旧传统,打破某个偶像及与其对应的陈规旧律时,因过分苛求而扫荡了不该扫荡的,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批评气质上,胡先骕相对超然一些,更尊重学术伦理,其批评观念明确而中正,与后来的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等暗相契合,他们多采纳批评必须宽容、独立、不诽谤、不攻讦的理念。通过与西方的比较,现代学者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诠释模式也作了批评,如茅盾曾言:“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9]强调文学批评也应该关注文学本身,以及文学技术层面的部分。胡先骕在《文学之标准》也有相应的思考,并力图使其规范化,他首先肯定了“标准”的重要性,“标准云者,先定一种度量,以衡较百物之大小长短轻重,而定其价值等差也。”“苟欲利用所谓科学方法者,亦莫不先求所以立标准之道。然则文学与艺术何可独无标准乎?”然后提出从“形”(字法、句法、章法,全书之结构)与“质”(内容)来规范“文学”。他认可的“形”为“文辞简练、字句精美、研炼精当、精洁严峻”,所以他批评文学革命派“以推翻一切古昔为文之规律为解放,遂全忘艺术以训练剪裁为原则;创‘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遂忘‘言有序’与‘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为文学家所必具之能事。”在“质”方面,他主张“礼”,“此所谓礼者,非具体之节文,而为社会中,人与人接时,所共守之节制是也。”即好文学须以“节制”、“中庸”为尚。同时“形”与“质”“二者相需为用而不可偏废,然有形者未必有其质,其质美矣,而其形或非,在为文者既求其质之精良,亦须兼顾其形之美善。”[10]也就是说,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成就佳作。批评家弗莱曾说:“文学批评之能成为一项系统的研究,其前提是文学具有一种性质确保这样的研究可能进行。”[11]胡先骕同样作了反证式的解读,从自己认同的批评标准来归纳、设定客体的性质、特征,提炼出评价文学好坏的标准。“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12]针对文学批评的主体、客体作深入的学理分析显示了胡先骕的理论自觉以及对文学批评自律性、专业化的吁求,因为作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文学批评假如缺乏独立品格即无真正的价值。以此为基础,胡先骕提出了超越性的批评精神,“今日宜具批评之精神,既不可食古不化,亦不可惟新是从,惟须以超越时代之眼光,为不偏不党之抉择。”[13]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茅盾1921年的担忧,“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14]无疑,胡先骕的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观点不免存在一些局限和矛盾,但是他秉持的立场方法和精神理念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对当时批评界有匡正之功效,至今也未失去可资借鉴的现实功能,尤其是他对批评的理性认同,独立品格的追求,以及对批评主体意识的重视,对当下的批评虚热症自有警示作用。
二、从胡先骕研究现状
论重写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一般来说,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书写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现代文学批评的时间区划,如确立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等;一是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即哪些批评文本、批评家值得研究,或者应该入史,以及如何入史。关于前一个问题有过一些争论,如温儒敏、周海波将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定在晚清,而许道明、高利克则定在“五四”,或《新青年》。但是后一个问题却不大为学者们所关注。其实,对此作仔细的甄别与严肃的思考极为重要,有助于解决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与书写中存在的缺失与盲点。如关于批评文本。不少学者认为现代作家、学者对现代作品的批评才能称之为现代文学批评,这就不免将现代文学批评的涵容窄化了。其实,现代文学批评至少包括两层意思: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现代的文学批评。自然,胡先骕那些推动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参与建构现代文学批评系统以及订立文学批评规范的批评文本就应当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了。再如关于不同派别批评家历史地位的衡定。通过以上对胡先骕的解读,可以肯定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应该拥有一席之地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文学批评理论史,他都是缺位的。以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例,学界对胡先骕及“学衡派”起初是盲视的,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5)都未予提及,直到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2002)才加于关注。其实,在现代文坛活跃过众多参与了批评活动的群体,如“学衡派”、“东方文化派”、后期“甲寅派”、《大公报•文学副刊》作者群、《东方杂志》作者群、《青鹤》作者群,以及早期“新儒家”等,他们多被排除在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叙述之外。根据文化属性,大体可以将他们命名为“文化守成主义批评群体”。概括而言,他们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特征:(1)思想上的反思现代性。出于对工具理性的反感,以及对西方文明陷落的警惕,他们流露出一种对“科学决定论”的怀疑倾向,力图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追求一种兼融中国文明与西洋经验的现代思维,并以此为基础,自主发展中国的民族新文化。实际上,这种反思视角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另一种体悟方式。(2)形式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羼杂,他们的讨论由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种文学现象引起,但最终均转入对新文(学)化的批驳,以及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热望。他们的批评实践同样有现实目的: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寻得转型之路。确实,他们的认知、观念对新文学(化)的建构发挥过映鉴功能,新文学(化)鼓吹者也以此为参照作过调整,重新接续现代与传统的赓承关系。由此可见,现代文学批评并非如某些批评史或论著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清晰、泾渭分明,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包容万有的场域。
至今为止,学术界都在试图以某一种理论作为支点来结构现代文学批评史,“现代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但是研究者对该概念并无严格的界定,反而作了单维体认,如有学者所言:“对现代性的单维体认作为一种价值预设,和20世纪前后的政治风云结合在一起,成长为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力量。新文化运动,作为激进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进行现代性追求的一次集中体现,就是以对现代性的单维体认为指针和航标的。”[15]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意义是固化的、确证的,甚至是合政治的,或合进化论的,那么它的丰富内涵及多样类型就丢失了。这也是他们未将“文化守成主义批评群体”视作研究对象的原因。先辈作家、学者如此判定,后世研究者亦是如此。在类似价值预设烛照下展开的现代文学批评研究自然无法摆脱这种话语权的宰制。但文化前行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单向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添补上“文化守成主义批评群体”,现代文学批评史才是完整的、立体的,关注他们有利于客观地还原历史,弥合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漏洞。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系统中,不同类型、倾向的批评都应该得到公平、合理的阐释与评价。自然,反思当下的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乃至于重写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了。
作者:廖太燕 单位:武汉大学 文学院
- 上一篇:中国文化融入现代设计的措施范文
- 下一篇: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分析范文
扩展阅读
- 1现代德育
- 2市场营销现代到后现代
- 3将现代因素融入戏曲现代戏
- 4现代文化
- 5传统与现代抉择
- 6剧院现代转换
- 7中国现代幽默喜剧
- 8现代后殖民文化
- 9现代广告招贴设计
- 10现代家具实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