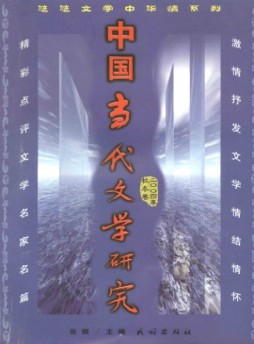当代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当代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当代哈尼族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是一种与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解放”叙事相反的叙事模式。这是一种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还乡”叙事,它强调对母族祖先的寻根、对原始自然和素朴人性的追寻、对原始宗教信仰和对某种神秘力量的暗示。
关键词:哈尼族;疾病与医疗叙事;还乡叙事;现代性
新中国初期(主要指建国后17年),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基本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解放”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家族祖先、宗教信仰、神灵观念、自然习俗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性一体化的异质性因素,被视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障碍,因而被视为人们致病之源,而现代性之科学、进步、理性等则是治病之策。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则基本上是另一种叙事——“还乡”叙事,这一叙事将现代性之科学、进步、理性等视为现代致病之因。而将少数民族的家族祖先、宗教信仰、神灵观念、自然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视为治病之策。当代哈尼族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反映的正是“还乡”叙事这一模式。
一另一种现代性叙事:“还乡”叙事
在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聚居在云南哈尼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被书写和形塑,如徐怀中的《买酒女》、季康和公浦的电影文学剧本《摩雅傣》等。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以内地汉族为主相对较为先进的现代文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造,表现将少数民族从疾病、蒙昧和水深火热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家族祖先、宗教信仰、神灵观念、自然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被视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障碍,被视为社会的毒瘤,成了疾病的隐喻。对身体的治疗就意味着对这些作为异质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去除,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现代性一体化工程的实现。当然也有体现民族特色的、对本民族疾病与医疗书写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在暴风雪中》、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白族作家杨苏的《山乡医生》、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思茅女儿》、蒙古族长篇叙事诗《牧人歌手唱达兰》等,但这些书写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写作中。“即是用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表现、整合少数民族题材,用进步的实践观念去规范少数民族生活,突出‘解放’‘进步’‘文明’‘发展’的主体,并因此实现启蒙、拯救的现代乌托邦。”[1]可见,不论是自我书写还是被书写,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都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解放”叙事,将少数民族从疾病、压迫、蒙昧无知中解放出来。
从1981年朗确的散文《茶山新曲》开始,哈尼族从此有了本民族作家。“哈尼族作家文学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近十年来展现出可喜的势头,它标志着哈尼族文学结束了没有作家文学的时代,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2]哈尼族作家开始书写自我,展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中形成了一个以朗确、哥布、存文学、艾扎、莫独、黄雁、艾吉、车明追、冯德胜、白茫茫、李少军等为代表的哈尼族作家群。尽管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作家群,但杨洪先生说:“哈尼族作家一出现,就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出哈尼族所经历的漫长的社会生活的历程,就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对哈尼族文化的深层思考中。”[3]这种思考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新中国初期不同的现代性视域,很多哈尼族作家以疾病与医疗视角来表达其对现代性的思考,思考现代性与家族祖先、宗教信仰、神灵观念、自然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朗确的长篇小说《最后的鹿园》、哥布的长篇诗歌《神圣的村庄》、黄雁的《樱花泉》、李批娘的《美丽的伤痛》、艾扎的《棺木》、艾吉的《清音》、李少军的《事与物•哈尼人断想》、陈强的诗歌《叫魂》等,这些作品体现出的是关于疾病与医疗的另一种现代性叙事——“还乡”叙事。“还乡”叙事也是一种现代性叙事,因为这一叙事本身就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强调在现代性一体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由此而生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民族祖先的追寻。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现代性不仅在初期对立于传统,经过发展演变的现代性也“对立于它自身”以及对立于现代文明之理性、功利、进步理想。这些哈尼族文学作品通过疾病与医疗的叙事来批判现代性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伤害与破坏,表现出对母族祖先、原始自然、素朴人性、原始宗教信仰、神秘力量等民族传统文化的皈依。
二对母族祖先的寻根
在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家族活动和对家族祖先的观念认同被认为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一体化总体设计相左的、地方宗族势力的意识形态,因而成为被禁止和消灭的对象,家族祖先成了社会疾病的隐喻。而当代哈尼族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则表现出哈尼族作家们对母族祖先的追寻,因为经历现代文明冲击和物欲诱惑的人们很多已经忘记了关于自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代哈尼族作家们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并将这一问题处理在疾病与医疗的文学叙事之中。对母族祖先的寻根意义重大,因为“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4]
“过了七十代后,他的子孙举行葬礼时,会让亡灵沿着祖先迁徙征途回归到诺玛阿美。还要举行隆重的开路仪式。……只有面对死亡,才能揭示出生的意义。哈尼族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却是用开路仪式来向后人指出生死的意义——活着就不断南迁,开疆拓土;死亡就回到遥远的北方,寻找祖先的足迹。”这是李少军先生关于哈尼族葬礼的一段叙述,哈尼族认为人死后灵魂是要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回归到祖先那里的。什么是灵魂?艾吉说:“魂就是你的脐带剪断了,但是你永远改变不了母亲流给你的血液的颜色。魂就是你的脚能单独走路了,但是你的脸庞上留下了父亲的永远抹不掉的脚印。……上升到我们民族的集体,它也在叫魂。祝愿远离它那颠沛流离,走在天边的儿女们的魂有遮风挡雨的屋子。”失去了对母族祖先的庇护和皈依,人是要生病的,生病是丢了魂了。于是就要叫魂,把游荡的魂魄喊回来。“在有人生千奇百怪的病,或亲人远行迟迟不归的日子……在迷雾茫茫的早晨,或黑幕渐渐合拢的黄昏。巫师或母亲们,在门口在野外,葫芦里装水,点燃一股细布绳。他们在叫魂:‘可——啦!唔——啦……’信口译成汉语,就是:‘快回来,回来。’……某人生病,是因为魂被鬼神拿走。”哈尼族诗人陈强在《叫魂》中写道:“在黄昏的暮景中/母亲在村口喊/喊那些时光灌醉的童年/喊那些做农活到月亮升起还未归的少年/喊那些漂泊远去的年轻人……/母亲是在给我叫魂/只要我在外漂泊一天/母亲就会给我叫魂。”为什么当代哈尼族会受伤得病、会失魂落魄呢?因为现代文明充满了进步、理性、金钱、物质等诱惑,许多哈尼族为此游走他乡、放逐流浪,受到诸多的屈辱和伤害。受伤的“我”需要母族的关怀和抚慰。母族始终是“我”精神的故乡,因为回到母族祖先的怀抱,“我”便内心宁静而安详,不再忧伤。
哈尼族认为,人是因为魂魄的丢失而发生疾病和伤痛的。丢失了魂魄,人就会像艾扎《阉谷》中形容的一样,不管是矿主还是砂丁都彼此残酷厮杀、人性堕落。因此,需要通过“叫魂”来呼唤人们对母族祖先的皈依,只有这样才能治疗因现代文明而迷失的病症。现代性之科学、理性、进步等反成了致病之因,而对母族祖先的皈依才是治病之策。
三对原始自然和素朴人性的追寻
在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疾病与原始自然、蒙昧无知相联系,疾病的治疗就是对原始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将人性从蒙昧无知中解放出来。而原始自然、蒙昧无知成为疾病的隐喻,现代性一体化对原始自然、蒙昧无知的改造和征服成了医疗恶性隐喻。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性之功利理性、进步理想等不断摧毁原始的大自然和美好素朴的人情习性,现代性成了现实社会的致病之源,原始自然和素朴人性成了治病之策。王洪兴的《家乡的小河》表达了对现代文明侵蚀原始自然乡村的担心和忧虑:“记忆中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家乡的小河边发现了矿石,乌黑中带有晶亮的沉甸甸的矿石。……外地人纷至沓来,原本是承包地和水田的地方,建起了不少工棚,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用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小河的宁静,打碎了小河安静的心。……家乡的阳光依旧,家乡的雨水依旧,可是家乡的小河流淌的水不再依旧。面对寨子的巨大变化,面对疮痍满目的家乡的小河,我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是该喜还是该悲……”现代文明不仅破坏了哈尼族世居乡村的健康和宁静,更是损害了哈尼族拙朴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水子的散文《故乡来去》中为现在哈尼族年轻人不再关心“昂玛翱”节日感到不快:“一百三十多户的寨子,却最终只有八名老者、两名中年人踽踽而来,他们代表十户人家。‘你晓不得,这几年去献‘昂玛翱’的并不多,就这十来家。’高哲大爹知道我的来意。‘不是说,除了年不好不能去的人家都去的吗?按规矩至少应该八九十户的。’我纳闷。‘谁想去谁就去,现在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不信这个了。’高哲大爹有些木讷。十个人中,其中两名中年人是牵头操办祭‘昂玛’的主人。‘今年是他们牵头,要不然他俩也不一定去,去年他俩就没来。’一名老者在旁轻描淡写说。为什么会这样?祭祀结束后,满怀遗憾地向我父亲问起原因。‘不知道,大家都是自愿去的。’父亲只是一个劲地干闷烟。”现代文明已经逐渐地侵蚀了哈尼族素朴美好的人情习性,而培养起了功利理性思想和实用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发生了改变。大多哈尼族作家表现出对这种改变的担心和忧虑。在存文学的长篇小说《兽灵》中,敦嘎、嘎斯和斯飘三代是峡谷里的英雄猎人,他们的祖先与大森林有着某种默契,森林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之所需——野猪、豹子、熊等野生动物,满足了他们当英雄好汉的心理,而对他们要求的回报是对森林的爱护和对野兽的保护。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他们逐渐变了,对野兽的捕杀越来越泛滥,武器越来越精良,规模越来越大,人与大自然的契约被破坏了。于是,自然开始惩罚人类。爷爷敦嘎晚年射了一只麂子,之后就神秘的病死了;儿子嘎斯滥杀猴群和野猪,最后被猴子和野猪弄死;孙子斯飘使用新式武器和大规模捕杀动物的捕兽网,最后在与一头野牛的较量中死去。“疾病”与“死亡”,这是历史宿命的真实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呢?很明显,小说希望通过疾病和死亡来说明尊重和善待大自然,保持素朴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任何单方面过分的物质欲望都会招致疾病和毁灭。
在朗确的长篇小说《最后的鹿园》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一个叫弄嘎的哈尼族山寨。在那里,人们有风一起挡,有果大家吃,没有哪一个人吃独食,这是“松命俄”(祖先名)传下来的规矩。“过去弄噶寨的男人进山打猎,只是为了发泄山里男人的一种野气,一种无畏和勇猛,表示一种男子汉狂放,寻找一种乐趣……没有把鹿茸、鹿胎、熊掌、熊胆、兽皮什么的放在心上,打来了就随意放着。”这里是宁静和谐的世界,有着自然素朴的生活方式和本真直率的人情习性。但随着私人商贩的到来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这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素朴的传统民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悄然发生改变。“可城里人三番五次地进山来买走这些东西,留给了他们一把一把的钱后,他们的心眼活了,眼睛也亮了……他们被钱深深地诱惑和滋生出越来越大的欲望,打破了这村里有史以来形成的那种宁静、安详、和睦、有好的氛围。特别是男人们,为了得到钱,他们几乎不再碰锄把,不再下田地劳动了,而是白天带着猎狗往树林里钻,晚上带着那神秘的头灯在山里转,疯狂地猎杀碰到的各种动物。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们的心也跟着变了,他们常常独自进山狩猎,打得野味回来也不让邻里寨人知道和分享,破了哈尼族见者有份的狩猎规矩。”人们不再安心到田间地头去劳作了,而是白天黑夜地到山林里围猎动物,最后甚至把整个三面山的林地和荒草坝都烧毁了,这火一直烧了十天十夜,烧得千年老林只剩下光秃秃的老树,只给荒草坝留下了乌黑黑的草灰。“最后的鹿园”不复存在了,这里乐善好施的淳朴民风也不复存在了。沙标的妻子明露发现寨里许多人的精神不大正常,还有些人生了怪病。小说最后借外来的商贩的口说出这一遭现代文明侵袭后的状况:“这些地方有好多病名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其中有种叫鹿癫病,听说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完全失去人的意识和控制能力,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会学着动物的声音叫唤,我看这里的人怕是得了这种病。”[13]现代文明摧毁了原始的大自然和哈尼族美好素朴的人情习性,成为哈尼族的致病之源。小说暗示:回到原始的大自然和美好朴素的人情习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才是这些病症的解决之道。徐培春的小说《古道》是一篇很有深意的文学作品,小说写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小兰(马润兰)不幸地和一个失去了性功能的男人(张大炮)在一起,而一个健壮的男人我(唐加顺)又错误地与一位癫痫病女人(山花)结合在一起。张大炮失去了性能力,不能有性的幸福和生育,给自己和小兰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最后他为救小兰失去了生命,山花因为癫痫病不断吃药而不能生育,以至于神志不清精神错乱。他人的死亡和衰废似乎顺理成章地成就了一对有情人——成就了“我”和小兰的结合和生育。在这里,疾病是现实客观的真实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呢?显然,作者意在向我们显示,社会的习俗和生理疾病在小说叙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线性的、向美好进发的历史进程的象征需要有疾病的存在,疾病成就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淳朴自然的民情风俗和美好素朴的人情习性是修复文明创伤的最好药方。
四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和对神秘力量的暗示
在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原始宗教、神灵观念与疾病相关联,原始宗教和神灵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用科学理性加以祛魅的对象。科学理性因为明显的物质效用而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但是当代科学经常被证伪和质疑,当性也越来越沦落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越来越成为一种人类自我异化的强大力量。“理智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透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和计算。”[5]哈尼族作家们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自我异化感,于是给世界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再加魅”,重新强调了宗教信仰和神秘力量的意义。在当代哈尼族文学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现代性之科学理性成了疾病的隐喻,而原始宗教、神灵观念则成了医疗的隐喻。哈尼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他们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由生到死、由盛到衰的自然发展过程,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和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而又能相互感应的;万物又都是有神灵附着的,哈尼族村寨都有其寨神山、寨神林、寨神树,这些都是保护哈尼族的神灵。人则都是有灵魂的,人死而灵魂不灭。这种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宗教观念为受现代文明伤害的哈尼族带来心灵的慰藉,也重新带给哈尼族关于疾病的认识。他们认为人生病是鬼神带走人的魂魄所致,诗人哥布在《神圣的村庄》写道:“当孩子们贪玩的魂魄/迷失在阴间的小路上/当老人们天真的魂魄/被邪恶的鬼神牵引躲藏/我(女巫)要到阴间神界找寻/把他们送回家里火塘边和神龛旁/……/寨神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当村里丢失的灵魂流浪/进入寨神的家不用担心/那儿有吃有喝回到自家一样/然而神界和人间毕竟不同/寨神让我(女巫)把魂儿们逐个送回村庄。”人们得了疾病是因为受到了邪恶的引诱,需要神灵来守护,这是一种疾病的“再加魅”。
在李批娘的小说《美丽的伤痛》中,男孩走出村寨到外面的现代城市里闯荡,带回来了男人难以启齿的“疾病”,男孩离开了心爱的女孩。男孩再也没有离开村寨,若干年后,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的“疾病”好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小孩。这神秘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偶然?是神灵?作者在小说中并未显示或说明。很明显,作者通过得病与病愈的安排,意在向我们表明现代文明是致病之源,而民族传统文化则是治病之策。男孩正是因为后来远离了都市现代文明,而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村寨里,所以他的病才得以治愈。这种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神秘主义的观念,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神秘性来肯定民族本土文化传统。艾扎的《棺树》同样具有神秘主义魔幻色彩。在小说中,“我”得了精神疾病,精神恍惚,总觉得棺树山上的棺树忽而发出不知是哭是笑的声音,忽而来到我的床前与我对话,盼我早死。棺树长得愈快,我就感觉到离死愈近,于是我在惊恐中一把火烧了棺树山。在哈尼族作家黄雁的《樱花泉》里,美丽的哈尼姑娘密娘被山外收皮货的商人用花言巧语打动而委身之后,却再也见不到皮货商的影子。密娘在樱花泉边生下的孩子掉进水里溺死后,就得了“花疯病”,成天疯疯癫癫,赤裸着身子在寨子周围荡来荡去。作者在小说里虽然有对母族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但同时作者也对外来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暗示密娘得“花疯病”是因为代表外来文明的皮货商人的始乱终弃,是他者文明对本土文明的伤害,因而只有切实回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怀抱里,人们才能获得健康和安乐。
综观所述,当代哈尼族文学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一反同新中国初期的解放叙事模式,而表现出对母族祖先、原始自然和素朴人情习性、原始宗教和神灵信仰等民族传统文化的皈依,这实际上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新定位。在当代哈尼族文学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现代性之科学知识、功利理性、进步观念等则成为致病之因,而家族祖先、宗教信仰、神灵观念、自然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则成了治病之策。在这里,拯救者成了被拯救者,现代文明成了人性自由舒展的牢笼,民族传统文化成了治疗现代性疾病的良药,无知无欲的蒙昧成了自然健康的存在,宗教神灵重新被搬上了神坛。“历史地看,决定论的机械宇宙模式和对偶然性的否定态度,促成了现代科学‘对世界进行祛魅’。……新的科学重新肯定了不可逆性和偶然性的地位,并允诺予世界一个全面的‘再加魅’(reenchantment)。”[6]现代性的洪水过后,露出的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在当代哈尼族文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叙事中,作家们对哈尼族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正面的书写,并参与到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重构之中。这实际上体现了哈尼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定位和在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红昆,欧之德.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20.
[2]史军超.哈尼族文学史[M].昆明:南民族出版社,1998:850.
[3]红河州文联.红河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选:骏马奖获奖作品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77.
[4]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03.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44-145.
[6]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90.
作者:杨运来1,2 单位:1.红河学院,2.厦门大学
- 上一篇: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面临的挑战范文
- 下一篇:历史文本下的现代影像叙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