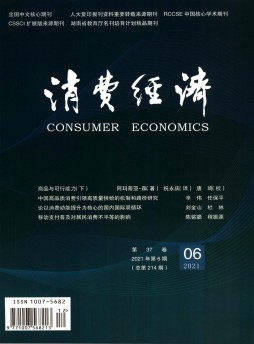消费文化导演现代悲剧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消费文化导演现代悲剧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内容摘要:本文从消费文化的角度,试图在经验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对《夜色温柔》中的主人公迪克走向沉沦的现代悲剧进行解读,并试图说明在一个克制变为欲望、勤俭变为享乐的消费社会里,主人公想通过虚幻而刺激的消费快感来建构身份和实现梦想,其结果必然遭到消费社会的控制和鄙弃。因此,迪克的命运是消费文化导演的现代悲剧。
关键词:消费文化《夜色温柔》迪克菲茨杰拉德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国“爵士时代”的代言人和美国文学“迷惘的一代”的杰出作家。在他短暂而忧伤的一生中,他的创作始终以人生的悲剧和幻灭作为主题,并以其独特的叙述,丰富的想象和诗性的语言倾力描绘了美国上世纪“喧嚣的20年代”欢歌笑舞的社会生活和浮华虚空的时代氛围。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美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却在追名逐利和纵情享乐中日渐沦丧和退化。菲茨杰拉德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物欲横流的社会,用深邃的笔触揭露穷奢极欲的内心。
一、“爵士时代”的喧嚣与刺激
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JayChapman)早在1898年就指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商业”(qtdinPizer416)。这里所提到的“商品文化”其实就是“消费文化”(consumptiveculture)。其典型特征就是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时尚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文化态度、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消费文化不仅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人们的行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尤其对人们自身身份的建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消费的驱动促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个人的价值、构建自我的尊严。每个人都要通过消费来建构身份和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然而,这也为社会带来了精神的危机。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欲望代替了克制,享乐代替了勤俭。一些人挥霍无度,炫耀财富,在狂欢作乐和玩世不恭中找寻生活的意义。正如维布伦(Veblen)在他的《有闲阶级》中所言:凭借自己免于劳动的自由和引人注目的公开挥霍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财富,来表现一个阶级超过另一个阶级的优越性(转引自霍顿爱德华兹265)。但是,无节制的满足性或者物质的欲望最终要通向悲惨之路。这种追求自我中心将使我们无视别人的需求,把人降低为玩物,将爱降低为欲望,将产出降低为娱乐,使我们看不到别人创造的奇迹,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因此,一些迷惘的文学青年在一战后的美国社会普遍感到了思想空虚、情感孤独和精神挫折,他们旅居欧洲,(中国论文联盟整理)自我放逐,并在吮吸欧洲现代派的文学滋养后发展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20年代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小说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大大促进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杨金才227)。其中的菲茨杰拉德就是这群“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典型代表。
菲茨杰拉德一生共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他曾在自传体作品《崩溃》(TheCrack-up)中写到:“我头脑中的所有故事都包含着某种灾祸——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可爱的青年走向毁灭,短篇小说里的宝石山炸得无影无踪,我的百万富翁也如托马斯·哈代的农民一样,是美丽的,注定遭到厄运的”。而他历时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也充分验证了这种悲剧性的人生体认。小说以战后美国“迷惘的一代”的骚动、失落与沉沦为主题,深刻揭示了在动荡不安的20年代美国人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异化感。
本文将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在经验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对《夜色温柔》中的主人公迪克走向沉沦的现代悲剧进行解读,并试图说明在一个克制变为欲望、勤俭变为享乐的消费社会里,主人公想通过虚幻而刺激的消费快感来建构身份和实现梦想,其结果必然遭到消费社会的控制和鄙弃。迪克的命运正是消费文化导演的现代悲剧。
二、《夜色温柔》的浮华与幻灭
人类的生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艰难历程。古希腊的悲剧大多描述高贵的英雄与不可知的异己力量相互抗衡的结果;莎士比亚的悲剧所展示的是一个信仰崩溃、理性丧失的混乱时代,如《李尔王》的父女反目,《哈姆雷特》的兄弟相残等。进入20世纪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物质繁荣、奢侈消费,但精神萎靡、道德沦丧的危机之中,因此,现代悲剧作品的批判指向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转向对人类普遍面临困境的审视。其突出作用是:展示人类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而20世纪的小说家也把小说描写的重心由环境转向人,转向对人的命运和人类生活的深刻思考。他们不再重视悲剧情节的描写而转变为重视悲剧心理的刻画;他们不再把悲剧的根源推诿于环境,而关注人类灵魂中的冲突和内心世界的挣扎。可以说,现代悲剧作品在表现内容和特征上都发生了变化,人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日趋淡化,而人在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时的心灵冲突则更加激化,即从自身无法掌握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天生性情所产生的心理冲突悲剧到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的悲剧。用奥尼尔的话说:“人与命运的冲突,以往是与神的冲突,但现在则是与他自己,与他自己的过去,与他所寻找的归属和企图的冲突”(转引自苏珊‘朗格407)。
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就是这样一部书写现代悲剧的杰作。小说描写了主人公迪克,戴弗(DickDiver)在生活经验支离破碎的状况下游走于欧洲,试图寻找完整的自我,追求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却走向沉沦的悲剧命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个体,迪克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中,由于社会分工精细,“其中的个人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但是,“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26)。正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使迪克不甘于自己的现状,不满于自己被社会所规定的功能,于是努力拼搏,积极追求,试图通过自己的奋斗跻身上流社会,达到自我完善。为此,他不惜一切去取悦别人,展示自己的风度,追求奢华的生活,努力获得上流社会对自己的认同,然而这种自我救赎的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无时无刻不在创造和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个体在进行消费以满足各种欲望时,实际上已经为资本所控制。迪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大肆挥霍,到处游玩,以为这样便可以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最终却陷入消费的泥沼中无法自拔,经济上无法独立,事业荒废,所有的理想都已成空,剩下的唯有堕落而已。迪克·戴弗的形象正是菲茨杰拉德所谓“遭到厄运的”“可爱的青年”,他的悲剧揭示了“美国梦”掩盖下的社会危机,揭露了上流社会优雅外衣下隐藏的残酷本质。
三、身份建构与悲怆结局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利亚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是一种“能动的关系结构”,其对象不仅是被消费的物品,而且具有针对消费者周围集体和周围世界的意义(226)。《夜色温柔》为人们营造了一个迷离的“周围世界”和“周围集体”——海滩与高楼、财富与奢华、俊男与靓女,爱欲与情场——无一不赋予人们飞黄腾达的想象,构建上流社会的迷离空间。消费文化使迪克·戴弗产生了幻觉,使他对现实与虚幻交错难辨。消费活动让消费者得到某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实现”的感觉。
海滩这一意象在《夜色温柔》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整个故事有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一片海滩上,而且,与海滩意象相联的休闲、旅游、享乐贯穿小说的始终。可以说,《夜色温柔》展现了一种海滩式的生活方式。
小说以描写一个位于法国里维埃拉(Rivera)的海滨地区开始,故事结束时的最后场景也是这片海滩——由海滩始,由海滩终。“这里已成了显贵名流们的避暑胜地”(菲茨杰拉德133),也是戴弗夫妇的主要活动场所。可以说,作者已经赋予了这片海滩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除了其本身的自然属性之外,它更是一种消费对象。对于尼柯尔(Nicole)、萝丝玛丽(Rosemary)之类的“显贵名流”们而言,海滩是身份、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海滨旅馆的豪华、温馨,沙滩上晒太阳时的舒适、惬意,海水中搏浪时的舒展与豪情,等等这一切只有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相当财富的人才可能享受得到。从这种意义上讲,海滩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了一个符号。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当商品以系列的形式出现时,它们已经超越了物品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4)。海滩与海滨旅馆、救生筏、帐篷、遮阳伞、耙子、铲子、筛子等一系列物品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串意义”。人们在此所消费的已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是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对迪克而言,海滩除了具有上述意义外,更是他追求自我身份建构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一个破落家族的最后一丝希望”(407),迪克一直在努力追求自我的完善,实现人生价值。为此,他“要做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254)。在事业上他也确实颇有建树,然而这并未带给他所预想的结果。在“喧嚣的20年代”,在一个拜金主义的实利社会,只有海滩上的悠然自得,奢华的生活,四处游乐,尽情享受,才意味着真正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同。事实上,“商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具体地说,这是自我或某个社会集团或阶层对于某种文化认同的方式”(周小仪16)。王宁在《消费社会学》一书中也指出,“消费者不仅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群体归属的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对人的群体归属进行划分,而且每个人自己也通常会为自己找到一个群体归属”(52)。从某种意义上讲,迪克去海滨避暑胜地消费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身份、地位认同的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就表示认同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迪克所做的一切,正是希望通过选择上流社会的消费方式来获得认同,从而建构自我。然而,他却因此而沉迷于感官的刺激与消费的泥沼之中。他越来越感到经济的拮据,他“渐渐地被汹涌而来的钱与物的洪流淹没了”(289)。跻身上流社会并未给他带来辉煌,相反,一只无形的手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他:“他衣冠楚楚,手杖也很高档,但他却像动物那样被奴役和驱赶”(213)。最终,迪克离开了海滩,他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与不幸——尼柯尔情感上的背叛,沃伦家族及整个上流社会的鄙弃,自身事业的衰败和自我人格的丧失,以及他在与这些不幸的冲突中通过自我放逐所表现出的坚强和抗争,正传达着一种悲剧性的崇高美。
如果说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是经验层面的自我建构的话,那么营造一个艺术的、审美的世界则是迪克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建构。他是一个怀揣着美好梦想的梦想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完整、优雅、唯美的世界。同尼柯尔结婚便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追求。尼柯尔本身的美丽就是一种审美体验:
她的脸可以用“常见的美丽”这样的词来形容,然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的强健
的脸架子最初是按英雄的模式来构造的,其面容和表情的独特和生动,以及所有;Z同
气质和特性相联系的方面,仿佛是根据罗丹的意图塑造成的,随后再雕琢出美丽来,而
且恰到好处,稍有闪失,就会无可弥补地损伤它所具有的力量和特质。对这张嘴,雕塑
家更是费尽心机——这简直是杂志封面上的丘比特之弓,当然,它与脸的其它部位也相
吻合。(145)
她的漂亮以及她所展示出来的少女渴望爱情的激情正是迪克所需要的:“这个几乎还没有得救的落难者却给他带来了一块神奇的新大陆”(259)。另外,尼柯尔的病又为迪克提供了一个拯救他人,创造“一个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高雅境界”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尼柯尔的精神病象征着整个上流社会的病态:乱伦,冷漠,自私,纵情享乐。“生活在迪克周围的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都各有各的毛病和问题:巴比·沃伦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喜欢异想天开,却又感情冷漠……音乐家艾贝·诺思是一个思想颓废,嗜酒如命的酒鬼……汤米·巴尔奔心肠冷酷,性格野蛮,没有政治信仰和头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基斯克有自我暴露癖……萝丝玛丽风骚冶艳,放浪不羁……”(吴建国211)迪克想要以自己的善良、正直、文雅、风度来治愈他们的病态,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面对现代人性分裂的状况,席勒认为只有“游戏”,即艺术才能使人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在《夜色温柔》中,迪克就扮演了这种自救与救人的角色。在精心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来达到自我的完整统一的同时,他也在试图拯救他人。在海滩上,当人们嬉戏玩耍时,“身穿肉色短裤的迪克手持钉耙庄重地舞弄起来,表面上看象是在清除砾石,而那严肃庄重的脸上却渐渐显露出保守着某种奥秘的滑稽感”(132)。迪克的这一形象正象征着多年来,他承担着清杂除芜、正本清源的任务。他在生理上、心理上拯救尼柯尔,清洗她父亲的乱伦罪孽,医治各种由于社会的疾患而产生的精神幻灭症。他慷慨地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给需要他的人们,直到情感耗尽。正如吴建国所说,迪克“想以健康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来医治和改善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病态……他怀着这个梦想执着地进行了十多年的努力,目的就是要将这个梦想雕刻成一件艺术精品……精神病学科的医生此时似乎已成了一名勇于闯荡禁区的艺术家”(209)。迪克要把美丽的海滩变做一个独立存在的审美空间。在这里,一切是那样美好,宛如一件艺术作品:“旅馆与它门前明亮的、跪拜地毯似的棕黄色沙滩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及法意边界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滩,随着海生植物摇曳出的圈圈细浪颤动着”(133)。此时的迪克已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
周小仪在《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一书中总结了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他认为,艺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升华与审美化,实际上是在粉饰现实。它遮掩了艺术
家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和处境,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必要的想象性的歪曲’。艺术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与他们所处的真实的生存条件的一种想象性关系的体现’,通过这一‘想象的’关系,艺术家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某种特定的意义,也给予了艺术家主体以存在的价值。因此艺术创作……是一种实践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创造意义,构建主体的过程,通过营造一个艺术世界……艺术家获得一种身份,一种确定性,一种存在感”(99)。对迪克而言,对审美世界的创造正是他对“身份”、“确定性”、“存在感”的追求过程,是他获得自我建构的途径。
正如周小仪在《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中所论证的,审美与消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形式比比皆是,它们大都散发着商品消费的气息。迪克的海滩(中国论文联盟整理)世界也是如此:“四把大的遮阳伞……一座便携式冲凉更衣室,一只充气的橡皮马”,这些就连萝丝玛丽这样的好莱坞明星也“从未见过”,“是战后问世的第一批奢侈品,或许也是为第一批买主所拥有”(147);迪克·戴弗夫妇的别墅——黛安娜别墅的花园里的花“就像出售甜食的商店橱窗里的糖制花朵一样晶莹玲珑”(154)。自然的事物也被赋予了商品的形象特色。这充分印证了杰姆逊关于“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的观点(161)。迪克的审美世界已经“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杰姆逊162)。审美已被物化,消费又一次占据了上风。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是通过对消费个体进行分化作用,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因素”(77)。个体在消费的同时,已经为社会所控制。因此,在消费社会中想要通过消费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达到自我建构根本就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是被控制得更加牢固。《夜色温柔》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如前所述,身处“喧嚣的20年代”,“想要挽救自己”(406)的迪克,试图通过消费进入上流社会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审美艺术空间以期达到主体的确定性,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意义,最终却不得不受制于消费本身,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正如周小仪所指出的,“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实是徒劳无益的”(251)。身心俱疲的迪克只能离自己的救赎理想越来越远,终日沉迷于感官刺激,事业逐渐荒废。他说:“我想我患了黑死病吧”(334)。他认为自己是个“完全沉溺于个人私生活的落伍的科学家”(194)。尼柯尔也曾尖锐地指出,他“过去常有创造的欲望,而如今似乎总想毁灭什么”(376)。因此,迪克的悄然离去是他命运的必然:人格、自尊与自我的逐步丧失,最终逃不脱由消费文化导演的悲怆结局。
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悲剧结局源自他自身的悲剧感,与他自身在爵士时代的生活经历相联系,其作品和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真实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他对消费社会本质具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因此,他对迪克·戴弗的“自我放逐”和救赎,对他的抗争行为都抱有赞同的态度。所以,他没有让迪克在沉沦中彻底堕落,而是让他走出“每一个现代人都可能困闭其中的温柔富贵却又消弭人生的精神牢笼”,表现出一种面对苦难和不幸的“自虐”式的悲剧抗争精神,这种自我放逐是对失去自我的重新寻觅,是对自我建构的重新审视,也是迪克以及菲茨杰拉德自己的人生体认的一次重大飞跃。
- 上一篇:斯坦倍克作品珍珠对人类生存境遇寓言化书写范文
- 下一篇:糖果店主中交换模式范文
扩展阅读
- 1居民消费与消费金融
- 2文化消费
- 3消费信贷下居民消费论文
- 4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 5能源消费形势
- 6家庭消费贷款
- 7境外消费
- 8旅游消费合同
- 9引领时尚消费潮流
- 10服装消费因素
精品推荐
- 1消费经济学论文
- 2消费主义的好处
- 3消费者品牌忠诚度论文
- 4消费者行为学结课论文
- 5消费陷阱论文
- 6消费主义的积极影响
- 7消费社会论文
- 8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
- 9消费效益论文
- 10消费观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