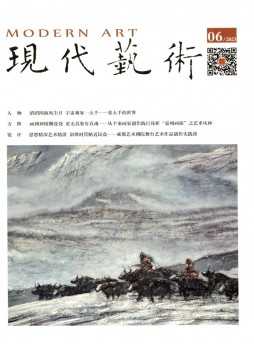现代后殖民文化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现代后殖民文化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格局。从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学者主要有罗青、廖炳惠、蔡源煌、邱贵芬、廖朝阳、蔡铮云、张小虹、陈儒修、曾庆豹、邓元忠等,台湾的后现代诗人作家代表有夏雨等,剧场创作者有钟明德等,郑明利主编过一些后现代主义方面的书,孟樊写过台湾后现代诗学方面著作。近年来,关注后学问题并从事后学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不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领域亦有新的拓展。其成果表征为翻译了不少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论著和文集,但直接就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撰写的专著却很少见到,大多是个别就西方后学某个专家(如德里达等)或课题进行研究。发表“后学”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主要有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中外文学》和《当代》等。本文主要打算通过对台湾地区的后学主要人物思想的探讨,对其“后学”地图和最近概貌有所了解,以展开进一步的思想对话。
一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路标
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于1989年在台湾五四书店出第一版。这部翻译和介绍性著作,是中国学者较早的学术翻译和研究著作,能够使人对当代西方和中国大陆港台的后现代地图有一个基本了解,值得重点评说。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
罗青[1]的代表作《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共分为七部分。其中:“导言”,作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纲要,分别简介欧美各国的后现代学术现状和学者思想,同时对台湾地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基本研究状况加以坐标式的定位,使人能够获得某种总体印象。“文学篇”,主要翻译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中的一章,使人能大略看到哈桑的思想。“艺术篇”,则主要翻译介绍莫道夫《后现代主义绘画》的思想。“哲学篇”,全书翻译了利奥塔德的重要著作《后现代状况》,可以说,正是利奥塔德这部重要的后现代著作的最早译介,使得罗青这部书具有了较厚重的学术含量。其后,“本土篇”,对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状况以及艺术发展作了一些描述。“年表篇”,则对欧美的后现代阶段和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加以罗列,使人能清楚地在时间的推移中把握到西方后现代和大陆台湾后现代的发生发展和基本轨迹。最后,“附录篇”列出了两篇对罗青该书的书评。
在导言中,罗青简要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基本发展态式,以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著述,然后概括地说明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就台湾引进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表而言,罗青认为,“台湾大约在1980年左右,开始引进‘后现代主义’式的说法。最显著的标竿是当年出版的《第三波》。……此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建筑、绘画……等等讨论,亦相继出现,在1986年左右达到高峰。该年,美国方面研究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学者如詹明信及哈山,先后多次来台北访问讲学。使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及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2]尽管美国的“后学”理论家到台湾并引起后现代文化艺术的论争,但是在台湾地区是否进入后现代的问题上尚存在着颇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有些则认为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这反映了台湾近几十年存在着农业、工业、后工业三者混杂的状况和处于走向后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这种过渡时期中,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一种对当代社会的阐释方法,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社会转型进行描述,甚至以后现代主义观点回顾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新的解释。正是这种泛后现代思维方式,使得罗?嗳衔泄糯丫泻笙执蛩亓恕!爸泄榉ㄔ谔铺谑保愠鱿至恕督医豸酥榇筇迫厥ソ绦颉氛庋淖髌贰U馐翘粕趁呕橙拾训笔惫绞詹氐耐豸酥榉ǎ燃右愿粗疲儆眉舻督夤钩筛霰鸬牡プ郑缓笾刈槌梢黄碌奈恼隆4哟顺鱿值幕准安噬子〖闫祝际抢谜庵指粗啤⒎至选⒅刈榈哪J嚼粗谱鞯摹C鞒鱿值某鞘性煸埃渤浞值睦昧舜艘患呛叛降哪D飧粗剖址ǎ讶瓤占浼岸瓤占渲械母髦肿恃兜ピ粗浦刈椋纬闪酥泄钤缙诘暮笙执浇ㄖ绺瘛!盵3]在这里,罗青大胆地将后现代的复制和拼贴手法,往前推到唐代或明代。但是问题在于,后现代不仅是一种复制重组的技术,而且是一种在后工业信息社会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信息传递方式,一种整体性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方式,简单地说中国唐代书法明代建筑已经“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后现代式”风格,恐怕会出现很多理论难点,而且这种过分地将西方他者理论本土化,也要冒一些时间空间上的巨大文化差异的风险。
在本土篇中,罗青用了三讲的篇幅展开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其中第二讲《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较全面地阐释了台湾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反映,其知识发展的方式获得新的突破,社会的价值观及生活形态朝向多元主义迈进。在思想解构中,所有的观念意义与价值都从过去固定结构中解构出来而可以自由漂流重组。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逐渐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从60年代开始,台湾在食衣住行、娱乐出版、生命遗传工程等方面都出现了后工业社会信息膨胀和标新立异的新症候。在音乐、绘画、文学方面,一些艺术家也改变过去的艺术思维方式,有意识地采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作品中的后现代表现因素逐渐增多,风格各异。罗青在此比较清晰地列出了台湾后现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对传统模式的解构式重组和多元共生式创造。
在罗青看来,后现代主义除了采用复制拼贴以及多元混杂的特征外,一个重要特色是把庸俗的世俗文化与严肃的精英文化融合起来,但是二者杂糅又时时造成矛盾的反效果。因此,在文化艺术中使大众通俗与严肃高尚相结合并未能成为后现代主义驾轻就熟的转型方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罗青坚持,在当代社会巨变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的转型:哲学上张扬解构主义思想而将传统的思想重新阐释和厘定;文学上关注后设语言而消解中心主义的价值模式;社会思潮方面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个人主义的特殊性的张扬;艺术方面则是创新的尺度成为整个领域的新规范,从而使任何僵化的体制和规范归于解体。后现代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突破了传统的篱藩,走出了一条在信息社会中的后现代的不归路。
罗青的功绩不在于他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本书的理论建树方面看,并不能称为是很厚重的。罗青的意义应该是:首先将西方的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翻译介绍到本土,使人能知微见著,从而使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研究走出了初期介绍的格局,将后现代的研究转入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推进了大陆和港台学者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他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后现代观念的正确把握,使中国后现代艺术具有了一个试验空间。这种翻译引介和身体力行地后现代诗歌绘画创作结合起来,显示出罗青的基本特色,当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提升和系统化的学术问题。
(二)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如果说,罗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研究从面上拓宽了后现代进入台湾话语场域的言路,那么,廖炳惠[4]则从理论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成为本土理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
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主义问题与现代主义有深刻内在的关联。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巴比伦塔在《圣经》中的地位有些诡异,它似乎在道出上帝的能力权威时又暗加毁损质疑,在表明人类的无能为力之时又暗示其逾越潜能。廖炳惠通过现象发现矛盾而使问题显豁出来:上帝使人的语言混淆是否为一种惩罚?对人而言这是损还是另一种得?或者是在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人与神、潜能与现实和辩证关系?廖炳惠从这里展开思想的论证,更深一层地触及到通天塔中人神身份问题和语言同一性问题,进而强调:“如果把追求统
一、新生的现代主义整个夷平是后现代之举的话,那巴别塔可说是后现代的源头了。……巴别塔的失利则让人类了解到未来及新的领域危机,同时体会到断裂与不连续性,人类从此各自为政,企图从统一整体建筑的废墟中走出自己的路。”[5]这一段文本意义分析,敏锐地看到了在寻求同一性与寻求差异性、寻求整体性与寻求零散性的人与神的根本思维裂痕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差异问题,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内在转换。换言之,廖炳惠认为,“后现代从巴别塔那儿找到了源头,哈伯玛斯想以理性的?骋蝗ブ亟ê笙执陌捅鹚钆匪⒌孪4锏热丝闯霭捅鹚蟮牡亩嘣芩恐髡糯又姓业饺擞肷系鄣男鹿叵怠!盵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以理性的同一获得语言的统一而重建人类理解的共识性的现代主义者,而利奥塔德和德里达则看到人类交流的差异性而张扬多元文化取向,这种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冲突的剖析,使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性和他者的权力性有了新的解构思维进路。从巴比伦塔这一角度切近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可以见到廖炳惠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着力点之所在。
在《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中,廖炳惠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曾在台湾风靡一时,如今则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但流行之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依旧是不甚了了甚至误解。有些张扬后殖民的人反复申说这类时髦话语,而另一些人则望文生义地动辄排斥,这两种人都未必了解后殖民论述形成的过程及其洞见与盲视。“一般人对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不是太轻易接受,信手拿来便套到台湾或用在任何遭到压抑的肤色、性别、阶层上;要不就是以跨国联盟的左派思想去驳斥后殖民论述,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契入世界之间的不均发展及更加恶化的跨国剥削。不管是采完全接受或彻底排斥,这两种学者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同时也没注意到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化理论的不适切性。”[7]廖炳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超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文化意涵,并在对西方学者傅科、哈伯玛斯、泰勒等有关现代文化的话语分析中,引申出台湾社会面临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对以下问题的实质做出审理。
其一,对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加以考察。后殖民批评家以“殖民主义”一词取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中惯用的“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检视帝国与殖民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殖民的延伸意义。廖炳惠认为,“随着新殖民与后殖民的并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传统,针对本土与环球文化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现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坚持文化差异。绝大部分的‘后殖民批评家’或‘后殖民知识分子’是在此种社会环境(越战及冷战结束)里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学、研究所,然后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国,形成其‘后殖民’观点,与欧美正崛起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彼此搭配,在推波助澜之下,俨然是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8]廖炳惠注意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构成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强调知识话语本土化和普遍性的双重性。这种殖民文化社群重新阐释自身的传统并确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亚洲,由于被殖民经验的错综复杂,使学者们在用后殖民的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与文学时,仍然受制于中心话语理论。台湾历史的艰难历?蹋沟闷湮幕臀难С氏殖鱿嗟备丛拥木肮郏庵指丛拥奈幕肮巯鲁氏值氖乔鄱辔男睦斫峁梗易魑斗肿樱谑兰秃笾趁裼锞持校哉庵置目坦堑闹趁窬凶呕坝锛费沟哪谠诖赐矗⒃诘贝幕芯康奈谋局斜碚鞒隼础?/P>
其二,现代化理路及其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使当代社会面临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混杂,个人的视觉与想像思维不断被大众媒体所诱导所左右。后殖民话语因为在东西方的不同语境而无法确定其普遍有效性,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台湾的文化分析,只能在局部分析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或有选择性地描述、解释或预设某些层面而已,无法深入洞悉台湾目前的文化状况。“从台湾来谈后现代或后殖民经验已不再那么简单,更不是提倡本土论述,扬弃理论,即能解决。要切入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争辩空间之前,我们得先整理一下后现代文化论述的脉络,并将这些理论与西洋现代的文化或政治形式作某种程度的关联。透过这种整理,我们或许会明白后现代的描述及先辈策略有其内在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出后现代论述如何将他人文化转化为‘正被弱势化’(minoritizing)的族群与风尚,以至于未能具体面对与自己完全同的其他社会。”[9]基于对后殖民理论有限性和西方文化中心理论的警惕,使得廖炳惠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设定限制,对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政治文本做出了一些理论框架性描述。在后殖民研究中,有必要探讨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多种正面与反面影响?绕湓诙远剿铮╞ilingual)知识分子或多语信息的消费与再生产行为的研究。在廖炳惠看来,这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在迈入新殖民主义的地区而又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如何针对本地的政治社会性和文化问题在跨国经济和学术架构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在国际公共场域的势力不断以媒体、技术转移、调查报告等方式形成国家政府和民族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应如何弄清这种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危机?(三)相应于日益频繁的解构中心解构经典与移民或文化交流等活动,非欧美的地区怎样翻译和运用其他世界的信息或将本土文化信息译介到欧美世界,其接受情况如何?(四)在逐渐国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凸显国际不均匀的文化政治局势下,艺术演出与公共话语如何定位并发挥其作用?都市及其公共空间如何呈现其新形象或功能?而面对这些变化,旧有的文化评论形式如何与逐渐丧失兴趣的本土大众或开始感到兴趣的外地文化社群产生互动?(五)跨国艺术赞助机构在促进某地区文化或政治形式的交流上怎样发挥其作用?在分列了上述话题之后,廖炳惠强调当代东方世界中,双语精英的出现使得后现代后殖民处境复杂化。问题还在于,后殖民话语大多是基于作为英、法、德、美的殖民地的非?蕖⒂《鹊鹊氐木椋胄矶嘌翘厍案厶ǖ陌胫趁窬椴⒉幌嗤R虼耍谒蠢矗拖愀刍蛱ㄍ宓鹊囟裕笾趁穹治鍪欠衲芄怀闪⒒故且桓鲆晌省?/P>
其三,后殖民与新殖民的关系。后殖民话语与新殖民话语当然不同,后殖民是一种解构殖民话语,而新殖民则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去文化殖民。在这一点上,廖炳惠认为,后殖民后现论毕竟是进口欧美的理论,为了避免盲目地陷入同时又不截然对抗后现代或后殖民的论述,需要对其加以反省:“(一)后现代(至少古典后现代)有其西方现代情境下的局限;(二)后殖民是在具体历史经验中发展出的论述,对其他社会不一定适用;(三)目前在亚太地区所发展出的双语(或双语以上)的资讯消费与再生产现象,已非这些理论所能掌握;(四)如何以亚太文化经验,在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差距之间,找出另一条路,至少对双语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个挑战。”[10]应该说,廖炳惠的这一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不少盲目推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者的理论误区,他在后学如日中天时看到了其对亚太地区状况产生的未周延性,在后学理论进入第三世界时抱持一种设界和划定有效性范围的学术态度,这使他能在具体论述中,不仅采用后殖民理论的有效性,而且能通过这一理论看到本土学者或双语精英的现实问题。廖炳惠在分析《刚下船的中国移民》一剧时,充分采用了后殖民理论的正面性效应,使其阐释能够知微见著,认为剧作者在此剧中写出了双重的后殖民问题,一是透过美国生长的华人来排斥刚来的中国移民,反映华人之间的族群差异所形成的彼此剥削现象,二是美国白人对华人移民的鄙夷,表现出美国本土内对于种族问题的暴力。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族群社会的矛盾,成为后殖民社会中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其四,有关后殖民理论不足及其困境。廖炳惠认为,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解存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反对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对“何谓后殖民”所指涉的内容(what)表示不解,进而质疑后殖民话语只是解构主义的解读策略。“不少是就‘何时可算后殖民’(when)及‘在何地发展出后殖民理论’(where),去抨击后殖民学者将各种仍处于殖民阶段的社会当作后殖民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是在欧美第一世界的菁英大学中高唱后殖民的论调,对第三世界里真正的跨国剥削、政府暴力、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日常政治视若无睹,甚至于以‘番易’、‘应变’、‘挪用’、‘创造性误用’的模糊辞汇,把具体的历史、社会事件加以升华、遗忘,以至于与后现代主义及环球帝国主义沆瀣一气。”[11]事实上,后学并不是第一世界的专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第三世界学者当然可以运用,但是不能将这种理论解构和修辞策略绝对化,而无视接纳与排斥的机制背后交织着某种殖民与后殖民的情结。二,就后殖民的历史脉络而言,“未能细究时间、历史的面向,不管新旧殖民或后现代的跨国活动均列为后殖民的范畴,而且也忽视后殖民理论代表之间彼此之间的明显差异,一律冠以同样的头衔。”[12]在我看来,?伪莸呐烙衅湎质嫡攵孕裕侵纸趁裼牒笾趁裰饕逡约昂笙执饕寤煳惶福虻サ赝吵莆翱诤呕酢倍唤姓嬲姆治龅淖龇ǎ得鞯贝踅缰械募虻セ鸵馄檬虑阆蚪衔飨浴?梢运担笙执笾趁衽兰胰泛醮嬖诓簧傥侍猓瞧淅砺鬯嘉椒ǖ某鲂氯粗档弥厥樱挥η嵋准右约蛩鹾颓狻6遥伪菟康鞯挠镅灾趁竦奈侍猓唤鲆鸶厶ㄑд叩墓刈ⅲ乙苍嚼丛揭鸫舐窖д叩闹厥印W魑恢钟镅栽靥澹颐抢碛Χ杂⒂锏娜找嫱卣沟奈幕┱判约右耘校遣荒芫环炊杂⒂锏氖澜缧越涣餍裕辈荒懿蛔⒁饽赣镂幕莸挠行院湍赣锝逃南质敌晕侍猓蛭庵挚床患暮笾趁窕坝锴阆颍锌赡苁褂镅猿晌幕趁窕蛭幕裰趁竦牧砝嘈问健?/P>
在我看来,廖炳惠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在台湾学者中无疑是相当有理论体系性建树的,这种建树建立在他清明的理性价值分析和辩证的逻辑方法上。他一方面,注意跨国现象中的概念隐喻及其文化分析策略,透视后殖民社会中的各种具体话语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另一方面,强调不能脱离当代中国自身的语境,应就亚太地区的多层殖民后殖民经验加以分析,建立相对应的新的区域研究模式。同时,还注意到后殖民研究中的种种误区,以及这些误区所表征出来的中国学界的内部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这种全方位的后殖民理论审理,使廖炳惠的后殖民分析中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微观的方法分析获得了较好的统一。
二后现代女性话语与殖民记忆
(一),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
女性主义在港台特殊语境中出现的问题与大陆学界的问题颇有差异,具体体现在观察问题的角度、理论出发点和文化话语角色的不同,以及站在世界文化角度看东方的层面不同,而且结论也大相径庭。张小虹[13]多年来致力于后现代与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代序”中说:“多年的深情投入孕育出了《后现代/女人》这本书,企图排列组合性别、权力与欲望的种种关系位置。后现代与女人间的斜杠,既是区隔也是流通转换的可能,标示着(后)启蒙模式与(后)性别研究中同时在于不在性别之中的吊诡。”[14]在我看来,张小虹这本文集比较广泛地讨论了当代社会一些颇为敏感的女性主义文化艺术问题,作者尤其注重电影和戏剧分析,使其理论没有成为一种枯燥的说教,而是成为有品位的话语描述。
在《东方蝴蝶:后现代的性别与文化差异》中,张小虹通过对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解构性阐释,力求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在叙述东方女性蝴蝶为自己的西方爱人无怨无悔的牺牲奉献之后,进一步追问道:“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西方特质/东方特质,《蝴蝶夫人》便建立在此互为映镜的二元对立结构上,而性别差异更平行于文化差异,父权统治对应于帝国霸权。此西强东弱、男尊女卑的权力阶层更进一步自然化、本质化弱势的一方:东方—女性天生温柔婉约、惟命是从。……于是我们可以问:蝴蝶这神秘东方的象征是否正反应着西方文化的权力投射与性欲幻想?这出东方女子对西方男子无怨无悔的爱情是否正影射着东方对西方统治的心悦诚服?”[15]张小虹接着分析华裔美籍剧作家黄哲伦将普契尼《蝴蝶夫人》这一西方话语模式加以改写的歌舞剧《蝴蝶君》,认为这出后现代蝴蝶传奇力图解构原剧中东西文化和男女关系的权力迷思,对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反讽。剧中法国外交官葛利马一厢情愿地将评剧演员宋莉玲想像为美丽娇弱的“蝴蝶夫人”,并表征出自己对东方夫人的深层误读和权力遮蔽。然而,这位夫人却深刻批评东方主义,抨击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性别与种族歧视。据此,张小虹发问道“这无能法国外交官的消极性误读不也出现在几位高明法国理论家含自我解构的积极性误读中吗?想想罗兰巴特笔下那象征‘无限阴性’、‘诠释尽头’的中国、傅柯文中那专擅艺术的古老中国、德希达所言超越理体中心的中国文化与非语音文字、或是克利思蒂娃心中那‘伊底帕斯前期’的原始中国”。[16]剧作者善于突显东西方之“内”的差别,同时厘定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提出异同共存的文化模式,将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复数化和不定化,使得这出戏剧成为西方主义对东方主义的一次文化颠覆活动。
在《〈红高粱〉中的女人与性》中,张小虹的分析进入了一个“如何在男人的世界里铺陈一个女人的故事”的新的问题层面。《红高粱》用粗野丑陋凶蛮来突显原始生命的勃发躁动,裸露原始感性生命欲望,在原始与文明、真实与虚幻、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寻求特殊的诉诸感官刺激的美感,从而在历史时空的荒野角落——文化边缘地带设立了一个东方景观。“在中国,旧礼教规范压抑着个体自由意志,窒息了民族的活力,张艺谋的一席话便是要创造一个能摆脱礼教桎梏,还我原始活泼的民俗文化空间,是要以一群丑怪粗大的蛮荒化外之民,展现原始自然活力与性欲本能”。[17]在张小虹看来,张艺谋在运用电影语言符号诠释民俗文化性格上,融野与文、粗与精、丑与美、蛮与柔于一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美感与风格,但同时又认为,要在男人的世界里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不容易,尽管《红高粱》展示了一个胆大坚毅的女性,但父权社会“性/性别”意识形态的阴影仍然遮盖了她的形象。
在“身体政治与文化抗争篇”中,张小虹的笔触进入日常生活层面,使得问题的揭示具有了多重视野。女性身体与被看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生存性和身体性关系的重要话语,这“身体话语”中从外控到内化种种权力网络的建立运作方式,对应了解福柯所谓“驯服身体”、“自我工程”的话语。而其从观念拟像到消费欲望诸多复杂的政治修辞,更可突显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政治观,以及社会控制和个体反抗文化批判的冲突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张小虹强调,一方面,必须给与后现代身体论述相当程度的肯定,不宜一味采用文化霸权或父权宰制的批判模式,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苗条话语中以女性身体作为主要监控对象、强化女性外貌为主要资本等现象做出严厉批判。因为女性身体话语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性别政治问题。[18]
也许,《审判“女性主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女性对话》,是张小虹写得最具理论色彩的一篇。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女权主义的困境不仅在于容易僵化的“主义”话语形式,而且当敞开其揭示现代生存普遍性的表面伪装后,女性主义往往又呈现出其中产阶级——异性恋取向——学院派中心的原形。本文从多方面厘清性别与种族复杂问题,探讨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之异同,在跨文化跨国界的讨论框架中重审以下问题: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以白概全”的假设以及全球性策略的缺失,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纠葛,第一世界女性“姊妹盟”的诉求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冲突。张小虹清醒地看到“白种女性要打入白种男性权力中心的同时,常常疏忽了这些争取到的位子是建立在种族歧视或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于是在男女分享权力的口号下,她们成为新的压迫者。当她们一心一意要发展新女性文化、打破传统父权桎梏的同时,往往仍是在欧美原有的文化架构中打转,忘了反省这架构中内存的民族本位主义与优越感。这些缺失推到极端,将使国际女性主义变成另一种新帝国、新殖民主义。”[19]这一看法尤为重要,因为第三世界妇女不仅在本?潦艿叫员鹌缡樱以诿娑晕鞣交坝镏行氖保乖馐艿轿鞣街行幕坝锏墓逝灾饕宓乃呋坝锏哪印R虼耍Ω们康鞯谝皇澜缬氲谌澜缗远曰爸薪ㄉ栊缘幕幻妫コ浠坝锍逋缓推缡拥囊幻妗5谝皇澜缗员氐弥匦路词∑淅砺劢ü褂胗旁叫奶谌澜缗砸残氩慰嘉鞣脚灾饕逯芯坑刖椋邮芩嵌孕员鹧蛊裙刈⒌奶嵝选=胂质祷坝锊忝妫判『缰赋觯栽诘苯裆缁岬闹堆爸谐渎宋侍狻8軦drienneRich(瑞琪)《朝向女性中心的大学》的说法,“大学教育为传统父权家庭的翻版,在行政系统中,权力中心(上自校长下自系主任)为男性把持,女性被排挤在外,在教学过程中,以男性思考方式为主宰,女性观点被压抑。……埋首书堆做研究报告的我们,既不能依据女性的观点做一个抗拒的读者,也不致力重新恢复遗落的女性传统——如女性史观、女性文学史、女性文化等。这些现象让我们不禁怀疑女性在知识殿堂内的存在,是否只是一种隐形的存在?”[20]这种直面台湾地区教育问题的现实的理论勇气,这种通过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分析当下自身的处境问题的批评实践,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大体上看,张小虹的研究,在女性主义的权力霸权话语中,保持了一份冷静清醒的理性,同时尽可能避免写得男性化的问题和话语表述方式,甚至有意识地破除男性话语的僵硬和板滞,而是以短小的篇幅、灵动的思想、丰富的例证、娓娓道来的女性话语,直觉般地将问题揭示出来。因而,这种女性主义风格和后殖民的边缘态度,尤其显得引人注目。
(二),殖民话语与电影帝国。
陈儒修[21]《电影中的台湾意识: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一文中认为,主体性问题无所不在,但是在后殖民时期,主体性则成为一个问题。他在讨论前,先对“后殖民”与“去殖民”的加以定义:“所谓‘殖民’,可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实践;‘后殖民’则为重要的论述场域,用以解释跨国资本主义与国族、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体性与文化认同等多面向的关系;而‘去殖民’则须视为被殖民主体行动的力量(与开始),用以脱离殖民经验所产生的困境。殖民的的概念出现在欧洲古老帝国在贸易与武力方面所进行的全球性扩张。其历史可追溯至十
四、十五世纪,一直到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可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验。”[22]在做出具体定义后,陈儒修对英法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的殖民统治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经营殖民地是为了要更方便地取得矿藏、输出原料和扩展海外市场。法国则采行文化同化政策,吸引菁英份子到法国求取知识并成为当地政府的技术官僚。“台湾的殖民经验又与上述的情况不同,日本之前的西班牙、荷兰等国把台湾当成军事据点,一切建设是想把台湾变成一座海上堡垒。到了日本政府时期,他们期望把台湾变成医院与谷仓,所以鼓励台湾留学生学医、学农,又与英国、法国不同。……殖民不单单是一个外来政权强加统治另一个民族,它促成社会结构的变化,通常是使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西方国家把他们引以为傲的艺术文化、基督教伦理、资本主义等概念带到殖民地,然后称之为进步的力量。”[23]这段话将殖民统治的区别加以分类化的研究,强调殖民统治在完成物质掠夺的同时,将文化殖民和霸权话语植入被殖民地区,造成对殖民者的经济和文化的依赖性,从而沦为宗主国的附庸,甚至在社会转型中成为宗主国“进步”神话的造神者。
在陈儒修看来,后殖民论述的“后”有着矛盾性的意义,即除了表示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以外,还意味着殖民经验的延续——殖民母国文化的霸权式影响,使殖民遗迹并没有因为殖民主人的离去而消失,这造成了殖民记忆的空间化。“后殖民论述细致的思考,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普遍的事实: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不代表该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等方面,已脱离殖民状态。……美国的文化商品,不论是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或者是可口可乐与麦当劳速食店,用着美国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做后盾,到世界各国攻占市场,可通称为文化帝国主义。”[24]陈儒修对殖民记忆的空间话话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的论述,尤其有新颖之处,这表明,后殖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延伸。后殖民情境并不止于殖民地独立之后所进入的历史时期,同时留下殖民经验与记忆铭刻于本土文化之内的痕迹,并与本土传统文化未曾变形的部分产生互动关系。因此,“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语言成为官话,每个人都得学习。到了独立之后,语言的使用可以凸显外来文化移入交杂的情形,每个人都变成双语使用者,例如在言谈间加入外来语,有时候用母语‘翻译’一遍,有时候则不翻译,故意保留意义的暧昧性,有时候则使用外来语法表达等,皆点出殖民/被殖民文化混杂的现象。……由于不再可能回到殖民前所谓‘纯净的’本土文化情境,后殖民文化的混杂特性,遂形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后殖民的文化认同将由此开始。”[25]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陈儒修注意到后殖民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混杂的文化,本土传统和外来文化、痛苦的记忆与现代性权力相交织,使得被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双语杂糅状态,显示出文化被抹擦,母语被介入,文化认同和文化拒斥混杂的新状态,而这正是第三世界文化和语言面临后殖民时代的真实处境。
陈儒修关注后殖民电影问题,因为这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尽管电影来自西方,但第三世界电影人仍挪用这种西方形式将电影与本土文化整合,逐渐扬弃其外在的西方中心标识,而表现自我民族的特有美学风格。“在时间与空间的面向,西方电影强调线性时间的延续,第三世界电影则重视空间的关系,所以使用大量的长镜头,让观众参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特写镜头出现在西方电影中,乃是为了凸显主角,或制造心理冲击,但在第三世界电影则很少使用这种镜头,因为他们不强调个人崇拜,主张集体行动。第三世界电影的例子说明了西方电影艺术与本土传统文化混杂共存的辩证关系,并且成为这些国家寻求文化自主的最佳典范。”当代电影作为后现代艺术形式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表现出中西方文化二元对立模式的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曾是被殖民奴役的人们心灵上最后一道桎梏,只有在不断整合中彻底清理,后殖民才能真正代表殖民历史的终结和新的整合性文化空间的诞生。
在我看来,陈儒修的研究表明了一种超越后殖民文化对抗性而走向文化整合性的努力。面对西方话语时,第三世界学者经常很尴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氛围,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获取和学习甚至“戏仿”西方的一些有效性话语。因为一些元范畴已经成为了人类思维共同的文化资本,变成每一个人都达到共识的基本言述方式时,只能加以采纳,但绝对不能不加分析地将西方话语装进本土文化思维框架中,而在后殖民时代丧失自身文化的合法性而成为西方话语的整体挪用。可以说,正是在解殖民过程中,第三世界不断消除自身的被殖民经验,找回自身的文化记忆,使得文化重建不是单纯回到过去历史文化的元生态中去,而是在新的文化整合中,生长出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既是历史的伤痕,又是新的历史建构的文化心理奠基。
不妨说,后现代后殖民的政治学视野使我们体认到: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化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且成为一种泛化的文化政治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在对当代社会现象做出某种文化阐释时已然看到,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选择问题已经同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这无疑表明,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和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后殖民知识分子还需学会协调国际政治关系并将“话语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
三后现代文化与宗教精神
(一),后殖民主义神学问题。
曾庆豹[26]大致上属于“哈(贝马斯)派”,曾经做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研究,以及哈贝马斯和福柯对权力批判的针锋相对议题。就后现代主义与神学问题而言,曾庆豹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阐述。
其一,神学话语的“语言转向”应是将语言看作“诠释的活动”。在他看来,这种神学阐释活动同一般的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的“语言分析”关系不大,而是注重检视语言的本性、及语词秩序借以表象其他语词的方法,把语言理解作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而进入神学诠释学论域。在语言上重新界定人与神关系,也展开在语言的作用中进入认信和灵修。“巴别塔事件是人的集体语言物化事件,因为人想在语言的作用上成为上帝而误入歧途,想藉由语言来满足欲望的工具,语言的可怕即在于它的创造能力,巴别塔的人是清楚这点的。语言作为一种作为创造力已然是人的集体潜意识,想在能力上证明与上帝的同等性,统一语言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7]在我看来,曾庆豹的文章将阐释学方法运用到宗教研究中,注重语言学转向问题在宗教研究中的回应,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在巴比伦塔的阐释上,持一种“人想在语言的作用上成为上帝而误入歧途”的观点,与廖炳惠对巴比伦塔中的语言问题的分析有相当大的差异,从这种差异中,可以看到人文研究和神学研究对人的地位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当然,曾庆豹将神学“语言转向”看作最终必须推进整体与之互动关系的“精神分析学”(人与自我的和解)、“政治经济学”(人与他人的和解)、“深层生态学”(人与自然的和解)的观点,还是有新意的。
其二,对现代主体性问题的怀疑。曾庆豹认为,“我怀疑‘天人合一’是和谐论的想法,因为它掩饰了权力的介入,更是伪装了合法化主体性哲学的支配性逻辑。”[28]在中国,儒家哲学与基督教文化在存有论方面,其根本不同在于“‘天人合一’与‘神人差异’的思想内容中,它们之间的不同事实上是逻辑的不同: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以及两种不同的方法:肯定的辩证法与否定的辩证法。存有论的不同引伸到人性论、实践论、价值学和文化理念方面也都不同。”[29]这里,曾庆豹将问题提到了权力话语的高度去审视,其中隐含的用西方的宗教精神消解本土的天人合一哲学精神的意向。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使其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抱有怀疑态度:“‘神人差异’的‘非同一性’并不因为反对主体中心而变成‘无主体’的价值摧毁,所以基督信仰一方面不同意‘现代性’的主体中心,也不接受‘后现代’对主体的无情摧毁,‘神人差异’所要导向的是‘互为主体性’的建立。‘非同一性’不接受将人实体化,也反对将上帝或神给实体化,因为这种结果都忽略了在‘差异’上所导向的交互主体性作用,神是主体,人也是主体,主体与主体的‘非同一性’原理防止落入中心主义,无论这个‘中心’是‘神’或‘人’,都在基督信仰的思想逻辑中说不通。”[30]曾庆豹强调,不能走回“现代性”主体性哲学或形而上学那种霸道,因为它已经证实了强烈的支配/权力作用之后果,而且,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提出了种种诘难,无疑是要驳斥思想沦为宰制工具的危险。这种反拨对主体性问题的审理有所砥砺。这种对现代性的警惕,正是后现代氛围中宗教学家的普遍策略性,当然,其中不乏价值关怀向度和宗教信仰维度的微妙差异。
其三,用解构主义一套话语分析当代宗教现象。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民族,……远离了本源和目地,远离了种族中心和人类学中心,在差异的裂变中使他者和边缘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流浪的天性强化了先知预言的力量,目的不是回归本源,而是经由书写的书写,痕迹的痕迹,暴露出弥赛亚的反叛性,颠覆性、不落入原地式的在场,以苦难和焦虑作为救赎的出路。”[31]这段话中,已经看不到太多的传统宗教的阐释,更多的是解构主义的术语,这种神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性,使得曾庆豹的论述中呈现出某种穿透性视界和感悟式语言,诸如:“被哲学视作愚拙,被宗教看为绊脚石,竟是通向信仰的途径。上帝在奥斯维辛的沉默是变得可以理解,他无计可施,他转过来要看看人的反应,要人为自己所做的承担一切后果。上帝不再成为形而上学屠杀的藉口,相反的,上帝要在受难者身上形成一股反抗的力量,批判那些以人之言替代上帝之言的血腥暴力,以挽救他者于宰割的边缘。在奥斯维辛之后思考上帝,他不再是希腊哲学产物下的‘逻各斯’而是‘肉身’、不是‘中心’而是‘他者’、不是‘对话录’而是‘圣经本文’。”[32]在我看来,曾庆豹善于通过哲学阐释方法重新阐释宗教经典和当代现象,他的哲学素养保证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人文科学和宗教神学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比照研究,从而显示出人的有限性和主体性的问题所在。[33]当然,正因为他将信仰加以绝对中心化和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轻视,使其研究具有了更明显的宗教布道性质,而不太注重学术研究的客观精神之维,这自然是由其研究的对象和自我的信仰所决定的。
(二),后现代思维与史学思想。
自从解释学风靡一时,对历史的客观论阐释和相对论阐释间就形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后现代阐释学将意义相对论推向极致,而成为一种主观论历史意义观。对此,邓元忠[34]在《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认为,“后现代主义运载现代性所选定的批判目标,订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和稳定性两点上,因而他们促使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历史的分期和对个人知行的意义等产生疑难。从很多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讽刺的、甚至绝望的世界观,其极端形式不容许任何传统史学的存在。从另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客观性和历史提出一些恼人的、但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特别击中了19世纪形成的科学与史学的要害,故科学和史学皆需重新整理反省过。”[35]邓元忠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进步发展观念的攻击,对知识话语和事物意义的客观性的否定,看作是一种“绝望的世界观”,但又对其批判终极真理和科学历史中的绝对理性观,表示首肯,认为重写科学和史学在后现代已经成为可能。在邓元忠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的批判十分积极,特别有关叙述与现代对时间的观念两点上。此批判牵连到‘历史消失’的看法,这是后现代想要颠覆历史时间的附带发展。它又连带到人权的观念、各种行业的定义、在政治与艺术中表相的可能性等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攻击史学上对现代的推崇态度。他们批评‘现代’史上出现的毁灭种族行为、世界大战、经济萧条、环境污染和饥荒现象,使得史学上所赞扬的进步、启蒙、理性不为可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批判所选定的目标有历史真理的性质,客观性与历史的叙述形式,至于控制时间的观念只是西洋帝国主义的历史意识对其臣属人民的强加之物。它并未真正提供如何得到解释、知识或了解的途径。”[36]在后现代只关注“破”而无视“立”的状况下,这种消解性的历史观,很难为历史意义的解释和知识生成的语境提供可靠的有效的阐释。在邓元忠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出于对“边缘”历史的偏爱,提倡发掘“下阶层”(Subaltern)历史,例如劳工史、移民史、妇女史、奴隶史、同性恋者史。但这种小历史很难与国史(大历史)合并起来写,于是,文化史开始接替社会史其地位而成为流行的写史方式。
邓元忠坚持:“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之后,最近十余年来现代化理论史学的立场已失掉广泛的支持,过去提倡理论的史学家如何接受文化史已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过去20年代中,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人数很多,但该学说的影响力,透过文学理论,愈来愈在文化研究的各种形式中增强。”[37]在史学界,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传统史学派认为后现论知识域的谬误干扰了史学领域;社会史学家因其空洞概念过多离社会状况太远而拒绝接受;而后现代文化史学家则认为后现代激发了史学界有关方法、目标、甚至知识基础的探讨兴趣。各种态度的差异性,表明了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正负面效应的不同侧面的把握和评价。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对史学界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其阐释文本的“滑动能指”的相对意义方式和语言模式,打破了传统历史解释的严格体制,使历史意义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而成为一个开放系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但是,“后现代主义否认任何‘本文’与‘上下文’‘因’与‘果’的可能区别。这种立场其实伤害了所有的社会理论。”[38]
这种所谓“后理论”,对史学知识论和批评论有着重新调整的功能:在史学知识性质的批评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并非实在——批评史学中的宏伟叙述和历史连续性话语,认定科学和史学所坚持的知识客观性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在史学方法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向历史叙述不可能表达真实,因为任何叙述方法背后都有着一整套意识形态的控制;后现代史学的论证方式祛除了只着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题材的偏颇,而强调“多元论”的多向度研究。可以说,邓元忠以敏锐的理论思维,注意到史学界后现代意义阐释新模式,尽管没有对这种模式的具体内容做更深的理论背景和基本形态的厘定,但是对台湾史学界的最新动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现代史学的正负面效应,以及运用这一理论的局限性,都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分析,使人能凭借这一“路标”,看到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向度。
应该说,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同大陆和香港的后学研究相比较,无疑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正如李欧梵所说的那样:“中国(大陆——引者案,下同)学者对于后现代在理论上争得非常厉害,但是并不‘玩理论’,这一点与台湾学者正相反。台湾学者对于后现论早在二十年以前就已进行介绍,而且每个人都很善于引经据典地‘玩理论’,诸如女权理论、拉康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其争论仅局限于学界,并不认为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中国(大陆)的学者则非常严肃,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甚至有人说后现论也有所谓‘文化霸权’这回事,要争得话语上的霸权、理论上的霸权,要比别人表述得更强有力,要在争论中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述得更有知识,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39]这种区别,在我看来,说明了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是一种学院派式的研究,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基本上成为专家教授的圈内话语。而大陆后学研究?率瞪细厥雍笾趁裰饕逦侍狻⒌谌澜缜熬拔侍狻⑽幕矸莸闹匦率樾次侍猓约爸泄率兰筒斡肴蛐远曰拔侍獾龋哂辛斯惴旱纳缁嵋馐逗椭泄执晕侍庋由煨灾省U窃谡飧鲆庖迳希彝饫钆疯笏档摹爸泄较执圆⒚挥型杲帷薄?/P>
总体上看,台湾地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既有对后现代主义方面的译介和专题研究,对后现代话语成为本土理论基本阐释方式的内在精神的洞悉,又有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在阐释当代文化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他者性和本土性、跨国资本与殖民记忆、语言殖民与双语精英等问题的前沿性分析,并且还有对女性主义处境与后殖民性别差异、后殖民政治学阐释、全球化语境中的神学问题、后现代史学中的意义重释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水平参差,角度各异,结论径庭,甚至观点对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西方时髦理论在东方的“旅行”中,有着怎样的变异和重写的特征,以及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变形——这本是后现代边缘理论和后殖民差异理论的应有之题。
当然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同大陆的后学研究相比,台湾对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圈内,没有引起公共领域的关注,因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台湾的文化身份问题等,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知识话语论争问题;其次,台湾仅仅将后学问题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因而对后学的讨论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成直接的作用,而基本上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学界的边缘,因而后学思想正负面效应的影响,都比大陆后学的要小,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当更为突出。
注释:
[1]罗青是一位后现代诗人和画家,出版诗集《吃西瓜的六种方法》、《隐形艺术家》、《录影诗学》等,同时还有评论集《从徐志摩到余光中》、《诗人之桥》等。
[2]同上书,第12页。
[3]同上书,第14-15页。
[4]廖炳惠,台湾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形式与意识型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北:麦田,1994年版;编《回顾现代文化想象》,台北:时报文化,1995年版。
[5]廖炳惠著《形式与意识型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5页。
[6]同上书,第300-301页。
[7]廖炳惠著《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北:麦田,1994年版,第5页。8]同上书,第18页。
[9]同上书,第62-63页。
[10]同上书,第69页。
[11]廖炳惠《后殖民研究的问题及其前景》,载简瑛瑛编《认同·差异·主体性》,台北:立绪文化,1997年版,第114页。
[12]同上书,第122页。
[13]张小虹,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
[14]同上书,第7页。
[15]同上书,第20页。
[16]同上书,第21页。
[17]同上书,第63页。
[18]参见上书,第104-107页。另可参阅其《子宫战场:女性与生育的政治文化意义》、《后现代母亲机器:人工生殖科技的醒思》等,同上书,第108-118页,第131-134页。在这些文章中,其体验式分析不乏新的思考维度。
[19]同上书,第148页。
[20]同上书,第183页。
[21]陈儒修,台湾艺术学院电影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台湾新台湾的历史文化经验》、《电影帝国》等。
[22]陈儒修《电影中的台湾意识: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载简瑛瑛主编《认同·差异·主体性》,台北:立绪文化,1997年版,第156页。
[23]同上书,第158-159页。
[24]同上书,第162-163页。
[25]同上书,第164-165页。
[26]曾庆豹,台湾中原大学讲师,有多篇讨论后现代主义与神学关系的。
[27]同上,第77页。
[28]曾庆豹《‘天人合一’与‘神人差异’的对比性批判诠释》,载《哲学与文化》廿二卷第二期,1995年,第141页。
[29]同上,第148页。
[30]同上,第145页。
[31]曾庆豹《形上学的终结与神/学的开端——卡尔巴特、德里达在后现代的路上》,载佛光大学编《佛学研究论文集》,1996年,第258页。
[32]同上,第259页。
[33]参曾庆豹《“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神学反思》,载香港《道风》;《形上学的终结与神/学的开端——卡尔巴特、德里达在后现代的路上》,载佛光大学编《佛学研究文论集》,1996年版。
[34]邓元忠,主要著作有《西洋近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西洋现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
[35]邓元忠《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5页。
[36]同上,第106页。
[37]邓元忠《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续),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4页。
[38]同上,第105页。
[39]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扩展阅读
- 1现代德育
- 2市场营销现代到后现代
- 3将现代因素融入戏曲现代戏
- 4现代文化
- 5传统与现代抉择
- 6剧院现代转换
- 7中国现代幽默喜剧
- 8现代后殖民文化
- 9现代广告招贴设计
- 10现代家具实现模式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