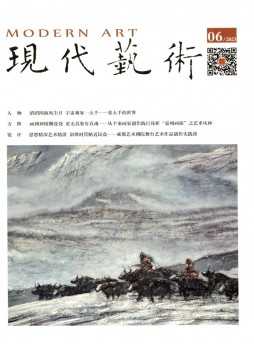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文学意识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文学意识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本文作者:曾令单位:存嘉应学院文学院
一近几年,以“重返80年代”为支点的关于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思考与讨论至今仍是个方兴未艾的话题,也产生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成果。不必讳言存在于这一讨论中欲将“重返”对象历史化与知识化的理想。但也不能否认这理想可能是一相情愿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其中还来不及过滤的焦躁心绪。而这一切,不管情愿与否,如今又都构成了我们谈论问题的具体语境。
在谈到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发生在80年代的那场社会运动是一个“拐点”,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次强力推进。其实它们同样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由80年代过渡到90年代的界碑。学界对于80年代与90年代关系的描述见仁见智。有论者用从“同一”走向“分化”,由“启蒙”走向“启蒙的自我瓦解”来描述。“如果说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是转为反思启蒙。”[1]12发生在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论争,最终使得在80年代建构起来的“同质化”世界彻底分崩离析,“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1]2他们为此还提出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封建化”与“割据化”情形,是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的:第一阶段(1990至1992年):《学人》杂志的创办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①,由此引起知识分子思考辩论是继续推进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还是通过反思,“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这一阶段的实质是知识分子经过80年代末的那场社会运动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即继续扮演公众“知识分子”角色,还是重返书斋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第二阶段(1992至1997年):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的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怎样重建自己的尊严,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论战①。“人文精神大讨论”是这一系列论战的轴心,也是在“同质化”的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界联盟在90年代分化前的最后一次盛会。第三阶段(1997年以后):由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发的长达三年的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②,其间讨论了现代性、自主与民主、社会公正、经济理论及民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刻,为20世纪思想史上所罕见。”[1]14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展开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论争的具体内容,而只能将它结合在与“问题”相关的讨论中。
“思想史”当然不等于“文学史”,但思想问题最终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反映在文学世界里。事实上在90年代“启蒙的自我瓦解”过程中,文学就在其中:或以作家———文化人的身份,或以作品———“中间物”的形式,与90年代的思想界无法剥离地交错在一起。如1990年代初在围绕“鲁迅风波”引发的道德理想主义论战中,“二王”(王蒙、王朔)、“二张”(张炜、张承志)等主要“当事人”都是文学中人;199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热”与“上海怀旧思潮”,既是文学领域的问题,但诚如有些论者所言,在关于“热”与“思潮”的相关解读中,又让我们看到了“殖民与后殖民理论的批判能量”;“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深刻介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展开,开启了文学重新回到当下的生活,打开了文学思想对当代社会文化未来走向发生影响的可能。”[1]109而2000年由话剧《切•格瓦拉》(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上演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关于“公平与正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告别革命”、“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等等,以及接着《切•格瓦拉》围绕《鲁迅先生》(张广天编导)引起的关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革命”的讨论,这些文学事件其实都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问题紧紧地关联在一起③。类似的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如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等等,对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因此我们既可以把90年代的文学研究看作是特定时期思想论战的延伸,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看作是文学在以其特别的方式介入90年代的思想论战。
二不过,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和关注的是体现这种研究姿态选择的一些具体个案。比如,启蒙“自我瓦解”的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究竟怎样影响着这一时期的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
在这一问题上,首先深入我们印象的也许是一些曾经在80年代执著于“迷人的理想”(穆旦诗)的文学研究者进入90年代以后不那么“自信”的“犹豫不决”。比如洪子诚,在谈到90年代思想立场的转变对自己文学研究的影响并在一些著作文章中存在的“互异”的情形时,他的“回答”便很能给我们启发:
在我看来,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理据,指出其意识形态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功绩,也不是说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评在“纯文学”的想象中过多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积极“回应现实”的“特殊经验”,也不见得应该回到文学“工具论”立场。指出“政治一开始”就在文学里面,也并非说政治(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可以穷尽、代替文学。在“世界(西方)文学”的背景下,重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异类的声音”,作为“小文学”的传统的意义,这也同样不是说要完全改变“十七年”和“”文学的描述图式。在中国,“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也曾具有活跃的创新力量。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在当代,经历了在“经典化”、“制度化”过程中的“自我损害”。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2]
洪子诚曾用“80年代残留物”这一深蕴自我反省意识的词句来描述自己的这种矛盾思想。但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启蒙的自我瓦解”后的投影。看到了80年代文学立场存在的过激的一面,但也不打算把当年的话倒过来说,甚至承认其合理性的成分,这本身固然可看作是一种“成熟”与“进步”,但同时更可看作是80年代“同质化”的思想界瓦解后的一种矛盾与困惑。这种情形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表现得更具体。在这篇文章中,洪子诚认为我们不应该把90年代以来(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研究中那种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行重新审察的情形看作是简单的“怀旧”,而应该看到这其中“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看到包含在其中的“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而这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在80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进入90年代后“真诚地忧虑”“人文精神的衰落。”[2]这情形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与当年关于“知识分子何为”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着更为可能的关联,当然也更为可信①。
富于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遭遇。还是在这篇文章中,洪子诚提到即使80年代充满自信、富于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式”的钱理群,在“思想割据”的90年代,也变得犹豫不决和矛盾重重,无法说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3]这些话由一个“义无返顾”于自己信念的理想主义者说出来,是比较“尖锐”的。洪子诚在文章最后这样总结:
这种种矛盾、困惑,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在认识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也因此冻结、凝固?[2]
看来,90年代,“自我瓦解”的不仅是思想的“启蒙”,同时也是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关于文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等诸多的问题。在80年代曾经被单一处理的文学图式,在价值体系坍塌后的90年代的思想碎片的闪烁光照下,显露出了其多元丰富的状貌。一方面想“坚持”与“不放弃”,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我们”因此“犹豫不决”,———也无法不“犹豫不决”。这种“犹豫不决”的姿态体现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对象(历史)时,是不再“斩钉截铁”地执迷于“非此即此”的价值判别,而多了一份“矜持”、“同情”和“理解”。由此,我们看到了在《1948:天地玄黄》“后记”中钱理群在处理“历史”与“历史写作”之间存在的“时间差”时的审慎,既“设身处地”又“毫不回避”,而不将历史简单化[4]326。也看到了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5]、《问题与方法》[6]、《当代文学的“一体化”》[7]等著述中对“当代”40至70年代文学图景描述时的“限度”意识。
三而也正是在90年代这样的语境中,如何面对包括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问题,得到了另一种与80年代不一样的表述。比如有些论者在“重构”包括40至70年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同时,试图掘取左翼、革命文学“遗产”中某些可靠的资源来滋养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藉此来表达对更宏大“问题”的关切,认为“能否冷静地认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既反对“‘非历史化’的文学倾向”(即“用现代化追求的‘误区’等流行意见来批评文学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但也反对“作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烈反弹”,“在‘怀旧’的心理中重温历史的激情,甚至表现出对革命时代价值观念的简单认同”的倾向[8]。作者甚至在文章中“无可争辩”地指出,50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学,曾经“发挥着其它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9]161,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和精神世界,指引他们这一代人“革命”。在新世纪初举办的一次“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研讨会中,有些论者把“启蒙”、“激情”、“回归浪漫”作为21世纪文学的“精神指归”,指出如何回到“民间”、“现实生活”与“文化的母体”,将影响到“21世纪文学质量”。“激情”、“浪漫”、“民间”、“现实生活”、“文化母体”等,这些都是20世纪左翼、革命文学曾经努力实践和追求的,同时又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启蒙自我瓦解”后我们文学和社会生活中所缺少的一些精神“钙”元素。有些论者在谈论左翼文学与“当下”的中国文学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感慨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已难再读到“浪漫”、“感动”和“理想主义”的东西,以及“批判精神”和“战斗性”[10]。
如果以上这些表达都还显得有些怀恋与失落但又不失温和的话,那么王富仁在2006年“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中关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左翼文学”的发言,其直面现实与人生的思考,则让我们看到了经过90年代的思想分化以后包括40至70年代在内的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何以值得关注的另一种“迫切”理由。他敏锐地洞察到了被隐没在当今“没有追求、没有争取、没有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的“和谐”学术背后一些不那么“和谐”,甚至有些让人“不安”的问题。王富仁甚至不惜暂时“放下”学术,直指这些年来频繁发生在中国高校中的大学生自杀行为,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我们”在给“他们”指出“美好的前途”、描绘“黄金世界”的同时,“把空白、把年轻人现在就应该懂得的人生的艰难,遮蔽了起来,使他们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到社会实践中去经受”,“而在这时,他们却在任何一个微小的痛苦面前都经受不住。”王富仁说,“假若是一个战士,我遇到困难我会克服它”,会因此变得更坚强。“只有这种坚强的精神,一种追求的精神,才能担当人生当中、历史当中、社会当中、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大踏步地走下去,走完自己的一生。不但走完自己的一生,同时为未来的人生留下一点儿的光明。假若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未来留下一点光明,我们的未来就会光明一点儿。”而这种带有鲜明的鲁迅式的精神品格与人生信念,正是曾经在80年代,直至近年仍残留在一些文学研究中所贬抑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学所具有的特质与内涵。王富仁指出,像30年代的那些左翼作家和他们所写的人物,当年曾经“在黑暗当中摸索着”,冒着被“专制”、被“杀头”、被“坐牢”的危险,“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尽管他们没有找到一条人类唯一正确的道路,他所相信的道路,可能他相信的一条所谓光明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被事实证明并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是,他们为了这条道路曾经挣扎过,曾经以自己的生命去实践。”而在“继续争取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道路上”都是“懦夫”的“我们”,对于这些精神文化遗产,不仅不予以继承发扬并让年轻一代了解学习,甚至简单地把他们押上“审判”与“批判”的历史舞台,确实让人感到“不安”。实际上,这其中关涉的已不仅是我们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样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在一种的态度中,“我们害了我们一代的年轻人”,“吃掉了年轻人”[11]。王富仁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其“问题方式”当然可以作进一步讨论,但我相信这些话是真挚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其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可以想象这些话在理想主义高扬的80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在当时缺乏自我反思的启蒙话语场景中,也很可能被视为“同质化”世界中的“异端”,甚至有可能与当时被极力批判的“文化”视为同类加以批判和否定。在经过“自我瓦解”的9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些话听来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与“犹豫不决”的“我们”比较,在清醒与冷静中,王富仁似乎多了一份执著与坚定;而与80年代的狂飙突进比较,则又似乎多了一份理性。如果不那么狭隘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视之为90年代瓦解后的思想界“成就”在文学研究中的另一种“收获”。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左翼文学几度沉浮枯荣,其社会意义与意识形态意义,亦“此一时彼一时”。但不管怎样,在“启蒙自我瓦解”以后的90年代重新讨论其社会意义与意识形态意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大的一笔遗产,我们如何处理包括40至70年代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甚至已不是简单的文学、学术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甚至还是曾经被我们不断排斥、剥离的意识形态意义①?若以此为话语平台,那么我们质疑90年代以后一些文学史写作中消解《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文学”的文学合法性的文学史观,便不应看作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之争了。
文学、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回应现实人生?我们讨论、研究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在90年代的思想语境中提出来,应该是个增殖性的问题。
四而在“40至70年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史”的讨论视阈中,我们几乎很容易便可看出,关于40至70年代文学讨论与研究的学科史意义的提出,只有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90年代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在90年代,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问题辨析清楚后,关于“当代文学”历史的写作实践才得以全面铺开,并呈多元分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入80年代以后因为高校中文学科课程开设需要有过一次编撰高潮。到90年代中期至近几年,则可谓达到了“全盛”期。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研究著作,“参考文献”部分列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88部,其中58部都是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推出的[12]359-362。这个数字,在说明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历史写作实践逐渐成熟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以为应该是蕴含在其中的(作为一段独立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写作实践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互动关系,即它们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消化着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论战成果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的清理,应该是我们考察讨论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与90年代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扩展阅读
- 1现代德育
- 2将现代因素融入戏曲现代戏
- 3市场营销现代到后现代
- 4现代文化
- 5传统与现代抉择
- 6剧院现代转换
- 7中国现代幽默喜剧
- 8现代后殖民文化
- 9现代广告招贴设计
- 10现代家具实现模式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