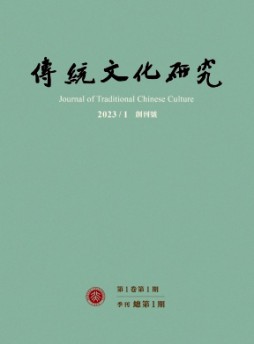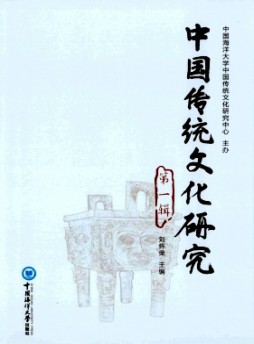传统文学透视的宏观批评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传统文学透视的宏观批评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本文作者:石麟单位: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一中国传统文学,如果从文化层面进行最粗线条的划分,似可分为“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市井文学”三大部分。所谓庙堂文学,实际上也就是正统文学,亦即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学;所谓山林文学,也就是隐逸文学,基本上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所谓市井文学,当然指的是大众文学。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庙堂文学是以统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群体意识的反映,山林文学则更多地反映了作家的个体意识,而市井文学则是另一种群体意识)))传统文化在广大民众中积淀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学虽然可以大体作以上三大部分的区分,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全然的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间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同样,对于某一位作家而言,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上述某一部分的文学创作。有时候他会从事庙堂文学的写作,有时候他又会进行山林文学的构造,有时候或许也会染指市井文学。有的作家甚至会同时进行多种层面的文学创作。从文体的角度看问题,则各种文体都可作为上述三大层面之文学创作的载体,但也有一定的侧重和偏向。如辞赋,写庙堂的作品最多,写山林者次之,写市井者极少;如诗歌,则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并重,只有民歌或拟民歌才写市井;至若词曲,大致上三者平分秋色;戏剧、小说创作,则市井第一、山林第二、庙堂第三了。
一个饶有意味的事实是,无论是庙堂文学、山林文学抑或是市井文学,都共同具有“辉煌”、“堕落”、“反思”三种创作状态,并且这三种状态有时相反相成,有时相辅相成,有时竟是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奇特态势。
二庙堂文学的辉煌是持久的,然而,这种持久的辉煌却建立在更为持久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进而言之,支撑辉煌的庙堂文学构架就是诸如忠、孝、仁、义、刚、正、廉、明等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粹。忠君爱国、孝养双亲、关心民瘼、信义待人、不屈不挠、正直无私、廉洁自律、明辨是非,以及要求建功立业、施展怀抱的人生追求,,这一切,难道不正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崇高精神吗?将这一切用诗词歌赋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难道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辉煌再现吗?《诗经》的周人史诗,屈原的《离骚》《九章》,孔夫子的《论语》,太史公的《史记》,那建安风骨,那正始哀音,左思的《咏史》诗,刘琨的《扶风歌》,陶渊明的“金刚怒目”,鲍明远的《拟行路难》,李、杜、高、岑的吟咏,韩、柳、欧、苏的文章,辛稼轩的气吞万里,陆放翁的铁马秋风,还有岳武穆、文文山、元好问、张养浩、于少保、陈子龙,,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笔下的作品,大多是时代的最强音。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用手中的笔、眼中的泪、心中的血,创造了庙堂文学的辉煌。
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下泪者不是忠臣,读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下泪者不是孝子,读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而不下泪者,此人大概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孝子。这是一种情结、一种积淀,一种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这里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思乡思亲的情绪,有正大光明的气质,有义无返顾的气概,,而这一切,又正是辉煌的庙堂文学之所以辉煌的底蕴。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这种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的心田。千千万万的正常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从小所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教育,有生以来就生活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浓厚的氛围之中。他们将这种正常的思想通过正常的方式表现出来,所缔造的难道不恰恰是庙堂文学的辉煌吗?
然而,当庙堂文学无比辉煌的同时,它的堕落也已悄然开始,甚至可以说,这堕落的根子就埋藏在辉煌的泥土之中。而这堕落是沿着两道轨迹前行的,一是歌功颂德,二是矫饰人情。
歌功颂德本来也没什么不好,但是,由对国家、民族、日月山河、英雄人物的歌颂转而成为对君王、上司、达官贵人的歌功颂德,却无疑是庙堂文学最大的堕落。在这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一一列举那些枯燥无味的“作品”,只看一点儿最极端的例子就足够了。明代洪武年间的文人吴伯宗这样写道:“唐尧虞舜今皇是”,“万岁声呼山动摇”。“江海小臣无以报,空将诗句美成康”。如此“诗句”,难道还不能体现庙堂文学的极端堕落吗?
除了对君王们进行直接歌颂而外,庙堂文学之歌功颂德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将传统封建道德推向极致并加以大力的歌颂和鼓吹。忠君爱国在这里变成了对君王的愚忠,孝养双亲在这里变成了割股疗亲一类愚昧而又残忍的行为,至于夫妻间的感情,则更是演变成为夫死守节乃至以死殉夫的妇女单方面必须履行的极端不人道的义务。总之,一切正常的人际关系都被冰凉、残酷而又极端偏颇的忠孝节义的道德信条所代替。我们且不说那多如牛毛的“家训”、“律条”、“烈女传”、“忠义传”等等,因为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文学作品,不在本文所论之列。我们也不说那些流传并不广泛的理学家们表彰忠孝节烈的诗歌散文作品,因为它们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在古代文学史上并未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只对宋元以降同时兴起的理学思想和戏剧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封建伦理道德的戏曲剧本略作分析,便可发现情况有多么严重。自元末高则诚在《琵琶记》中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标准之后,明代文人利用戏曲作品来宣扬教化、训诫人心之风便愈演愈烈。有的要求乐户女儿要“立心贞,出言准,守清名,志坚稳”,“到身后标题个烈女魂。”(朱有火敦《香囊怨》)有的高标作戏曲要“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丘浚《五伦全备记》)这便是戏曲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庙堂”之作,而且是走向堕落的庙堂之作。
辉煌的庙堂之作所表现的往往是人们的真情实感,而堕落的庙堂之作则往往以矫情代替真情。这样,就造成了“人品”与“文品”的极不协调,乃至极大的矛盾。因为屈原、杜甫忠君爱民的诗篇流传千古,因而人人都想写一点《离骚》《北征》那样的作品,于是乎,“今之学子美者,处富贵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谢榛《诗家直说》)这种矫情的表演便出现在既缺乏生活感受又要显得大义凛然的无聊文人们之间。甚至有些品行极其低劣的人,也在其诗文作品中摆出一副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悲天悯人的架势。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读两篇作品:
“泥污后土逾月余,四月雨至五月初。七日七夜复不止,钱王旧城市无米。城中之民不饥死,亦恐城外盗贼起。东邻高楼吹玉笙,前呵大马方横行。委巷比门绝朝饭,酒垆日征七百万。(方回《苦雨行》)“农田插秧秧绿时,稻中有稗农未知。稻苗欲秀稗先出,拔稗饲牛唯恐迟。今年浙西田没水,却向浙东籴稗子。一斗稗子价几何?已直去年三斗米。天灾使然赝胜真,焉得世间无稗人!”(方回《种稗叹》)如果我们不知道宋末元初的方回是何许人,大概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大概是一位杜甫的继承者吧。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方回究竟何许人也。据《癸辛杂识别集上》载:“方回,字万里,,其乡处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遂一向寓杭之三桥旅楼而不敢归。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知严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囊。”就是这样一个大节有亏小节损的“稗人”,居然写出了那样一些关心民瘼、忧愁乱世的诗篇,居然在自己的诗篇中大声疾呼“焉得世间无稗人”。这种貌似奇特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止一个方回,如潘岳、阮大铖等等,均乃如此。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以矫情的方式在掩盖着自己的劣行。毫无疑问,这也是庙堂文学的一种堕落。
当庙堂文学逐步堕落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或无聊文人的矫情载体之后,自然有人会对这一切进行反思,并且,一部文学史也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反拨中才得以前进的,庙堂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庙堂文学的反思的立足点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道德、传统学术的怀疑与否定方面。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怀疑,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又对明人的游谈无根进行了批判。至于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怀疑和否定。黄宗羲在《原君》中居然敢说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话,真乃石破天惊。被封建士大夫奉为人生信条的“文死谏、武死战”,却被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宝玉之口说成是“胡闹”,真是对传统道德的大不敬。如此等等的悖逆言论,在明末清初以降的文人那儿可谓屡见不鲜。正是在这种怀疑传统、否定传统的思潮的影响下,才会出现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粱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秋瑾这样一些反思型的作家以及他们所留下的极具启示力的优秀作品。从而使庙堂文学不仅没有走向彻底的败落,而且展示出黑暗王国的一线新的曙光。
三山林文学也有它的辉煌,它是长居于或暂居于草野的文人的心灵的歌。许多古籍中所记载的隐士是山林文学的文化原型,老庄哲学是山林文学的理论基础,逃避现实而又未能真正忘情于现实是山林文学作家的心理矛盾,贬谪罢官是山林文学缔造者们的经常性待遇和创作诱因,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山林文学创作主体的心灵慰藉,而美丽的大自然则是停泊这些痛苦灵魂的宁静港湾。
在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虽然也能找到山林文学的片断,但真正有代表性的山林文学作品却诞生于两晋以降。陶渊明、谢灵运、谢玄晖、王绩、王维、孟浩然、刘禹锡、柳宗元、林逋、苏轼、朱敦儒、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马致远、张养浩、贯云石、刘因、王冕、唐寅、王磐等,他们或以宁静清虚的心态来对待穷愁潦倒的生活,或以深入细致的描绘来展现如诗如画的美景,或在对山山水水的描摹中显示出无比深邃的哲学思考,或在对花花草草的勾画中体现了无比崇高的人格追求。这里有怀才不遇的牢骚,也有参透万物的旷达;这里有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洞天福地的朦胧憧憬。这里还有贬谪情结、遗民情结、悯农情结、游子情结,,所有这一些,他们用诗、用词、用曲、用赋、用长篇、用小品,总之是用一切文学样式来表现。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山林文学的辉煌,哪怕是潜藏在深山僻野间或士人心灵深处的辉煌。
山林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充分体现作家的个体感情和创作个性。表面上看,这些作品创作于山林之间,并以山林作为描写对象,而实际上,作品却融化在作者心中,甚至可以说写的就是作家自己。正因如此,他们无须戴上假面具,也无须刻意追求什么社会效果、艺术效果等等“身外之物”,而只是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地写来。这里有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也有大小谢的山水吟咏。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或描摩山水田园或抒发人生感受的的赋作辞章,如《江赋》《游天台山赋》《闲居赋》《恨赋》《别赋》《桃花源记》《北山移文》。这里还有那人生的哲理探寻和深沉叹息,如《春江花月夜》如《代悲白头翁》。在这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充满禅趣,意境空灵;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则充满生机,淳朴自然;就连豪迈的李白和沉郁的杜甫也偶尔到山林中“反串”。在这里,还有韦应物、刘长卿的山水之作,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的贬谪文学,还有自《水经注》发脉、至柳宗元《永州八记》而发扬光大、直至明清两代而盛传不衰的山水游记作品,还有宋词、元曲、明清诗歌中歌颂山林抒发感情的成千上万的心灵的乐章。对于山林文学的作家们而言,这一切都是他们心灵的自白,也是他们与“自我”的对话。充分真实化、充分个性化,同时,也充分孤独化、充分理想化。正是这一切,造就了山林文学的无比辉煌,哪怕是潜藏在心扉胸臆中的辉煌。
是的,充分的孤独化和充分的理想化造就了山林文学的辉煌。但是,过分的孤独化和过分的理想化又造成了山林文学的堕落。郊之“寒”、岛之“瘦”、姚合之“峭冷”,已经开始了由幽静的山林向着冷寂的深渊的下滑,而滑到“幽深孤峭”的钟、谭那儿,则已到了“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钟惺《诗归序》)、“必孤行于古今之间”(谭元春《诗归序》)的地步。这样的诗,实在不知道还要写它做什么!过分的孤独化,所磨灭的不仅是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灵性,更是人的生活热情、百灵之长的灵性。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文学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要恰当而真切地表现或反映这种结合,只是不同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各有其偏重而已。过分地强调群体性,是造成庙堂文学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分地强调个体性,则容易造成山林文学的堕落。
超越可能性的理想其实就是幻想,是麻痹自己而又麻痹他人的幻想。在古老的中国,幻想往往又与宗教、迷信、崇拜紧密相连。而这些幻想反映在山林文学的作品之中,就是那些消极避世乃至追求长生、寻求解脱的游仙诗、玄言诗、禅悦诗、冥悟诗,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代佛、道立言的宗教之作、迷信之作如“传灯录”、“证道书”一类的东西了。游仙诗的渊源虽可追寻到《离骚》,但那是一种积极的“游仙”,或者说,是借游仙表现作者心灵的远游,屈原可从来没有离开、也没有想到要真正离开尘寰世界。魏晋以降的游仙诗的作者们,才真正幻想着高蹈轻举、一步登天。稍后,玄言诗也不甘示弱,从老庄那儿借来了“物我同游”,从释子那儿借来了“虚心静照”,更加上士人们既有闲又有钱、既离尘且脱俗,于是淡乎寡味而又清高孤傲地“玄乎”了一个时代。用幻想代替现实、以玄言描述世界、这恐怕已接近山林文学的尽头。但是,比起那些用长篇叙事的方式来演述宗教、迷信的戏曲作品而言,游仙诗、玄言诗之类,又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号称“万花丛中马神仙”马致远,给我们留下的七个剧本中竟有四个是“神仙道化”剧。而元代的神仙道化剧竟是一大科,并影响到明清两代。就连汤显祖这样杰出的戏曲家,在他的“临川四梦”中竟也有一梦“佛”、一梦“道”,梦到了那远离尘世的虚无缥缈的世界。
在山林文学经历着朝过分孤独化和过分理想化两大方向堕落的时候,也有一些作家在这一最能表现文人自身情绪的园圃中苦思、沉吟。并且,在新的起点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在何景明“领会神情”认识的影响之下,在谢榛“自然妙者为上”理论的影响之下,在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之下,由晚明而及清代,形成了“性灵”一派。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到袁枚的“性灵说”,不仅使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山林文学的创作。晚明的小品文,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真性情同时也最富于创作个性的一批作品。晚明的游记作品,亦堪称纯情的作家与纯洁的大自然紧紧拥抱的结果。这里也有逍遥、也有放任、也有清高脱俗、也有自命不凡,但无论作家们心灵的航船向何方漂移,总是没有脱离尘寰世界。而且,在许多晚明小品文、游记以及此后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不少在抒发性灵的同时,含有深邃的人生哲理,那就更是山林文学中的珍品了。
山林文学,是封建时代文人心灵的驿站,但这驿站绝非建立在九霄云外,而仍然是悄然屹立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四市井文学的辉煌源自市井,因为它是“市井”文学。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南北朝乐府、到唐代的声诗和词,其中有不少市井之作。但市井文学的鸿篇巨制却毫无疑问地产生于宋代。关于宋代市井文学发达的原因,过去有着多方面的探讨,如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等等。但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宋代的城市格局的改观。相对于唐代比较封闭的坊市分离制的城市格局而言,宋代那种开放性的流线型的城市建筑格局应该对市井文学的繁荣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更兼之与唐代实行宵禁的制度相比,宋代不仅不搞什么宵禁,甚至是鼓励人们夜间消费,瓦舍勾栏动辄容纳数以万计的顾客,有的茶肆酒楼则几乎通宵达旦地服务。在如此肥沃的市井文化的上壤之中,市井文学的花朵为什么不能开得绚烂多彩呢?
在宋元话本、元人杂剧、明清传奇、明清章回小说、拟话本小说以及明清民歌时调中蕴涵着大量的市井文学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市井文学的辉煌。而市井文学辉煌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了与传统思想大异其趣的市民意识。宋元话本中写得最多也最精彩的是男女爱情故事,而且是市井男人与市井鬼女的爱情,《碾玉观音》如此,《志诚张主管》如此,《闹繁楼多情周胜仙》亦乃如此。因为现实世界中的恋爱不自由,因此就出现了如此多的市井中的人鬼之恋,市民们就是这样想问题的。元人杂剧中亦多爱情故事,表面上看,多半写的是公子小姐之间的爱情,但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市民趣味。《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惊梦”,《墙头马上》中李千金之私奔,《倩女离魂》中张倩女之离魂,都是在千金小姐的面貌掩盖之下的市井妇女行为的真实写照。
爱情,在封建时代,是统治者不准谈、文人偷偷谈、而只有市井小民才敢于公开谈的一个话题,故而才在市井文学中有如此多的爱情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爱情、婚姻、妇女的态度上,市井小民们自有与封建士大夫们截然不同的观点。“三言”中有两个名妓)))杜十娘和莘瑶琴都希望从良,都在选择对象。其结果,杜十娘选择了贵族公子李甲,因而怒沉江底、月缺花飞;莘瑶琴则选择了市井小民秦重,因而夫妻和合、花好月圆。这两篇作品似乎在告诉读者,真情不在贵族公子们那儿,真情在市井之间,在市井小民之中。这里所表现的难道不正是一种市民趣味吗?难道不是市井小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能够被人们所了解、所宣扬、所歌颂的一种历史性的要求吗?更有甚者,市民阶层不仅希望在市井文学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而且更渴望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他们对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妇女问题的新的道德评判。《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就是这种道德评判的一个形象载体。当蒋兴哥得知妻子王三巧有了外遇以后,一是自己承担了部分责任:“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二是委婉而体面地休妻:“本妇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因念夫妻感情,不忍明言,情愿退还本宗,听凭改嫁。”三是被休之妻再嫁时居然送去礼物:“兴哥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这些行为,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点之上,那就是把女人、哪怕是犯有过失的女人、哪怕是犯了在封建时代男人尤其不可原谅的过失的女人当作“人”来看待。这其实是一种人道情怀,一种在达官贵人不曾有、在封建卫道士们不曾有的人道情怀。尊重人性、尊重生活、尊重感情、尊重生命,这些市井小民们新型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明清两代的市井文学作品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小说如此、戏曲如此,民歌时调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中成百上千的作品,更是如此。
市井文学辉煌的标志绝不仅仅是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那市井百态、那江湖风波、那每天开门离不了的七件事、那形形色色的三百六十行,,其间酸、甜、苦、辣,涩,应有尽有。要想知道这市井生活的五味瓶究竟有多少内容,你可以去读柳耆卿的词,去读关汉卿的曲,去读《水浒传》,去读《金瓶梅》,去读“三言”“二拍”,去读元明清的杂剧、传奇,去读陈铎的《滑稽馀韵》,去读那些宝卷、弹词、子弟书。那里面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日常生活,什么叫市井中人的日常生活。市井文学的堕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宣扬封建迷信,二是鼓吹封建道德,三是欣赏畸形性欲。明清章回小说和拟话本小说中都有大量宣扬宗教迷信的低劣之作,长篇的如《扫魅敦伦东度记》《阴阳斗异说传奇》《天女散花》等,短篇的则有《雨花香》《通天台》等集子中的许多作品。所有这些,都体现着市井文学的末流向着世俗宗教迷信的堕落。鼓吹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在明清通俗小说尤其是拟话本小说中大量存在,只要翻开《石点头》《型世言》《西湖二集》《八洞天》《娱目醒心编》等拟话本集,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愚蠢的、反科学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或啼笑皆非的,总之是各种各样的忠、孝、节、烈、仁、义、友、信应有尽有,而且毫不含糊。至于色欲描写,更是某些市井文学作家的拿手好戏。在某些戏曲作品、甚至是比较优秀的戏曲作品中已开始出现过分的色情恶谑,到了小说创作、尤其是晚明小说创作中,这种不良倾向愈演愈烈,乃至不可收拾。《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有一定篇幅的色情描写是人所共知的,而情况更为严重的作品则有:章回小说中的《浪史》《肉蒲团》《绣榻野史》《浓情快史》《昭阳趣史》《株林野史》《杏花天》等等,拟话本小说中的《宜春香质》《弁而钗》《一片情》《欢喜冤家》等等、这些作品、或写女色、或写男风,真是人欲横流,体现了人的原始动物本能的一面。
市井文学的反思并不是由市井小民来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市并小民的思想积累之后再由那些穷愁潦倒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文人来完成的。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往往极端贫穷,而精神领域却极其富有。如董说、如李玉、如孔尚任、如吴敬梓、如曹雪芹、如李汝珍,,直到梁启超。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也大不一样,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对社会、人生、历史、现实有着深刻的思考,并且利用最为通俗的文学样式表现出来。“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做-眠仙阁.哩!,,只是我想将起来,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风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宫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这等看将起来,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尘。”这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在国之将亡的时候,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预感和悲哀,写到作品之中,就是董说的《西游补》。褒扬忠臣、反抗权阉,最有力量的是谁?是市井小民。市井小民所发动的苏州民变,代表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将这种思考搬上戏曲舞台,就是李玉等苏州派作家创作的时事剧《清忠谱》。思考,来自丰富而痛苦的现实生活;表现,却在那通俗而动人的市井文学之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高呼“一代文人有厄”而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创造了一个“女儿国”,在那里寄托了作者怀金悼玉的历史悲哀;李汝珍也勾画了一个“女儿国”,在那里却寄托了作者男女平等的朦胧理想。至若梁启超等人,则干脆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公开提出要依靠市井文学来改造社会、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市并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示了它巨大的威力和无尽的潜力。因为它所反映的已不仅仅是过去、现在,而且指向了恒远的未来。
五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市井文学的划分不过是我们为论述问题的方便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严格而言,任何类别的区分都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或者说,有许多文学作品并不能仅仅属于哪一类,而任何一位作家也不大可能一辈子只写某一类作品。陶渊明不仅有“悠然望南山”,也有“刑天舞干戚”。白居易不仅有“新乐府”的创作,也有“闲适诗”的撰写。苏东坡则处庙堂而忧其民,处山林而思其君。关汉卿的戏剧常以市井文学的方式反映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而他的散曲则更多一些山林文学与市井文学相结合的趣味。蒲松龄则既写堂堂正正的庙堂文章,又写雅俗共赏的《聊斋志异》,还写了充满世俗意味的俚曲小戏。至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佥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通俗小说中的伟大作品,则更是市并文学、山林文学、庙堂文学诸多因素的结合,只不过各有其侧重点而已。
对传统文学进行文化批评,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原本就深深扎根于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泥土之中,而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其民族性。不注目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学的影响而孤立地研究传统文学,其结果,只能是丧失其民族性。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无论是庙堂文学、山林文学抑或是市井文学,都拥有过各自的辉煌,也曾出现过各自的堕落,最终,也都酝酿着各自的反思。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辉煌的极端往往是堕落,堕落的尽头往往是反思,而反思,又往往意味着新的辉煌的即将到来。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市井文学均乃如此,三者之间的关系亦乃如此。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