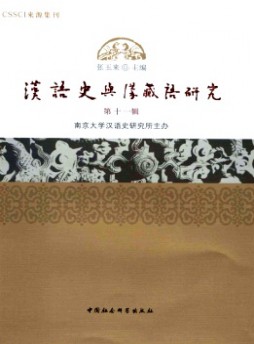汉语文学书写的语言困境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汉语文学书写的语言困境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前些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WolfgangKubin,1945—)对当代中国文学曾有过一个比较激烈的论断,在他看来,当代汉语文学在整体上水平都不高。顾彬先生的这个意见到底该如何评价,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话题。但真正值得重视的其实应当是他为这一结论所给出的问题,概而言之,就是“文学”和“语言”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顾彬先生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写得太快”,“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之一,我觉得是不知疲倦,写完了一本以后马上写第二本,每年都能出新作。”二是多数作家都“不懂外语”。“写得太快”说明作家的语言表述很顺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障碍、阻隔、迟疑、迷惑、焦虑或者恐惧等等之类的现象出现,而“不懂外语”则意味着客观上汉语作家已经阻断了与其他语种作家之间直接的对话、交流与联系;由此,当代中国的汉语文学写作就变成了“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的自言自语”。某种程度上说,顾彬先生所暗示的这种状况也许才是需要引起汉语作家高度重视的关键。
一、“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我们通常所谓的“汉语写作”其实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说法。就当代中国作家的具体创作而言,“汉语写作”主要指的是“普通话写作”,但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普通话”、“国语”、“母语”、“华语”、“白话”和“现代汉语”等等,这些具体的称谓之间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差别的——比较一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和欧美华裔作家的“汉语文学”文本,将会更为明显地体味到这种语言表述上的差异——当然,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和曾经的英美殖民地所使用的英语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差异。尤金•A•奈达(EugeneA•Nida,1914—2011)认为:“在许多语言中,经常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书面语言要求的准则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从而越来越远离了口语用法,文学方言最终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交流,从而也就出现了一场突发的语言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文学语言的标准就进一步接近了口语的标准。”现代形态的“汉语”源于民国初年由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白话”,“白话”的对立面是“文言”;当“文言”成为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学交流的最大障碍时,语言变革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正是在“语言变革”的意义上,“白话文运动”才成为了汉语“新文学”产生的标志。基于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经验的启发,为了配合建立以“语言/族裔共同体”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需要,在“白话”的基础上,中国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们合力发起了一场持续性的“国语运动”,即充分调动科研、教育、传媒及政令等几乎一切手段,从“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两个层面来普及和推广“国语”。
那么,什么是“国语”呢?胡适当年曾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述,他说:“我们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他同时又强调,“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朱希祖也曾明确表示:“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此二事,皆非用现代的语言不可。……吾人之所以创新文学,实不满意于旧文学;吾人今日的新文学,过了百年千年,后人的智慧日进,必不满意于吾人所创的文学而视为旧文学。所以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换句话说,朱希祖和胡适等一代“五四”学人对于作为“共同语”的“国语”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国语”和“新文学”其实既不是现成的东西,更不是由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们所制订的规范,它们都需要在“创制”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生成”出来——“生成”出了“新”的语言也就自然“生成”出了新的文学;而新的“文学”的创造同时也就促成了新的“国语”的生长与成熟。
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创制”出“新”的语言呢?就当时的具体境况来说,途径之一就是对既有语言资源的充分利用,其中包括文言汉语、旧式白话汉语、汉语民间方言、日制汉语新词,以及欧美等外来的翻译语言等,钱玄同即认为:“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国语的杂夹古语和今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国话和外国话而成,正是极好的现象,极适宜的办法。”周作人也肯定地说:“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途径之二则有赖于文学作家们面对这些语言资源时的创造性发挥。如鲁迅所说:“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
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一方面,民国时代作家笔下的语言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杂糅”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杂糅”,能够体现出“现代”意味的“国语”才逐步由过滤、提炼渐至走向了纯化和成型,胡适等人当年希望藉全新的“语言”标识来确认和建构“中华民族”自身族类身份的诉求也才得以实现。回顾这段历史所能得到的启发就是,“国语”绝不是对作家自由言说的“束缚”;甚至相反,要想使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能始终保持活力,恰恰需要“国语”本身的不断更新,而这份责任和义务更多的就需要“作家”去主动承担。
二、“普通话”书写的潜在意味
事实上,在整个“国语”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作家和语言学家们都曾产生过有关“国语”的统一是否会形成对于“文学”的束缚等等的顾虑。俞平伯说:“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学,不但要使用活的话语来表现它,并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我赞成统一国语,但我却不因此赞成以国语统一文学。”黎锦熙也曾明确表示:“何谓‘国语统一’?又含有两种意义:一曰‘统一’。二曰‘不统一’。”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国语,乃是全国人民用来表情达意的一种公共的语言,人人能够说,却不是人人必须说。……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的一种。”“总而言之,统一的国语就是一种标准的方言;不统一的方言,就是许多游离的国语。各有用途,互相帮助,这就叫‘不统一’的国语统一。”民国时期对于“国语”与“文学”关系的这种定位也可以看作是“国语”本身的开放性的一个证明。
如果说“国语”是一种始终处在“创制”过程之中的开放的“未定型”语言的话,那么,相比而言,我们当下所称的“普通话”恐怕已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普通话”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国语运动”初期就已经有所使用,但现在的所谓“普通话”概念则是根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来定义的,即“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应当说,这一界定在总体上延续的是民国时期以“国语”为“民族共同语”的基本思路,不过,我们如果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稍加回顾就不难发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普通话”的这一界定其实是附带了相当程度的限制性隐形规定的。在语音层面上,“北京语音”所指的并不是那种带有民间意味的鲜活的“京腔”,而主要是指用于官方传播媒介的“播送式语音”——代表性的样式就是电台、广播、电影及后来的电视等的语音范本。“播送式语音”以其特有的严肃性和正统性一直占据着“普通话”语音的主流,甚至在逐步构建起来的语音等级序列中始终处在了某种不言而喻的“高位”状态,由此也最终形成了对于其他语音形态的压制,比如,带有地方语音痕迹的“普通话”往往会因为“不标准”而容易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标准“京腔”对于“边地”方言的排斥等等。作家李锐就曾明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最高等的语言,而我们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任何一个方言来写小说,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土得掉渣。”
就“语汇”层面而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实际上同样是带有高度选择性的,即所有用语不得偏离官方主流语汇的既有规定,而一切异质的意识形态语汇、身体语汇、个性化的抒情语汇等等被划归为“语言禁忌”范畴的语汇,全部都处在“被剔除”之列——选择性的语汇规范完成的其实是一次“语汇清洁运动”。再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的角度来看,用于教育和普及的“白话文”也从来没有偏离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定要求,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从小学到大学所使用的语文教材的选本篇目即是最为突出的明证。所以,与其说是“现代白话文”确立了“普通话”的“语法”形态,还不如说实际上是报刊媒体的“政论式语法结构”奠定了“普通话”的“语法”基础。无论是在语音、语汇还是语法层面上,与民国时代人们对于“国语”的定位稍加比较就会明白,现今的所谓“普通话”从诞生之时起就已经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定型”语言了。王力在当年就曾明确表示:“国务院发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我们拥护这一个指示,我们协助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
“这里没有强迫命令,只有号召,然而这是政府严肃的号召,我们应该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北京的声音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我们要做到人人爱听中国声音。我们预祝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全国人民都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经翻译,眉飞色舞地听取总理的政治报告。”“普通话”的“定型”取向是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性的,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随着这种语言的日益普及和推广,“普通话”自身所具有的语言惯性已经使我们几乎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封闭性和程式性了。比如在讨论本属于“文学”问题的场合,我们能经常听到诸如“解放前/后”、“三突出”、“抗美援朝”、“精神文明”、“新时期”、“和谐社会”、“接地气”等等,大量的意识形态语汇已经完全渗透且融化在我们的日常表述之中,以至于我们似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意识形态意味及其与“文学”之间的距离了。接受一种语言范型实际上正意味着全面接受了这种语言所蕴涵的全部概念和价值指向,“文学”如果以这种语言为载体来展开“表述”,虽或“顺畅明了”,且富有“时代”特色,却必将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
三、“间性语言”与文学书写
优秀的作家常常既是语言的守护者,同时也是语言活力的激发者。乔姆斯基曾说:“语言能力最突出之处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的创造性’。”洪堡特也认为:“只有当精神投入到纯粹的思想生成之中,而思想的生成始终依赖于纯粹形式的兴趣时,观念才能真正充满活力地发展起来。在一种未能习惯于把形式当作真正的形式来表称的语言里,这种纯形式的兴趣是不可能被唤醒的,何况在这样的语言里,纯形式的兴趣也不会觅得惬意之所。因此,纯形式的兴趣一经苏醒,就要着手改造语言;而一旦语言以另一途径采用真正的形式,纯形式的兴趣则被突然激起。”要想摆脱既有“普通话”书写的束缚,汉语作家就需要去寻找既有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语言作为参照,以此才有可能真正激活其自身对于语言“纯粹形式”的兴趣。顾彬先生希望当代中国作家能够学习掌握外语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他借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身无彩凤双飞翼”作比,说:“掌握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一翼,掌握了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另一翼。拥有了这一对翅膀就能飞得高、飞得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翼,飞行的高度、距离都是有限的。我想,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论是着迷于本国文化的人,还是着迷于外国文化的人,都可以从‘双飞翼’这个概念中受到启发。”已故作家王小波曾有过一个说法,他认为,当代中国最好的汉语其实是“翻译语言”,他举的实例是王道乾先生所翻译的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和查良铮(穆旦)先生翻译的《青铜骑士》。他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
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尤金•A•奈达认为:“译文从来就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不存在永不过时的译文,这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翻译悖论之一。语言和文化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且,语言是一个开放系统,词义重叠,界线模糊——这可堪称逻辑学家的灾难,诗人之幸事。为了创新,为了获得通过符号对人类经验进行再解释的新的认识,对语言的不确定性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讨论都涉及到了“语言”的“跨界”问题。更深入一步来看,所谓“翻译”活动,无论是“归化”(domestication)还是“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语言”本身实际上始终都处在一种微妙的“间性”(interlanguage)状态——它随时都有可能向其本身的“母语”游移,但惟其如此,它才真正保留了“语言”自身的“活性”;游移的“不确定”及其可能产生的“多义性”有利于其对“语言定型化”的排斥——这一点恰恰与“文学”自身的“非确定性”特征相吻合。如哈蒂姆(BasilHatim)和梅森(IanMason)所言:“一个符号从一个语篇(起始点)旅行到了另一语篇(目的地)。从语篇到语篇所经过的地方,就是我们将所称的互文性空间(interte-xtualspace)。正是在这种空间中,附丽于这一符号的各类价值系统得到了调整。这就是说,引语的语源的符号价值经过转换,以便适应其新的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作用于新环境。”由翻译活动产生出的新的文本,我们可以称之为“间性”书写。而事实上,不光是“翻译语言”,现代的“汉语”本身所面对的多重资源都有可能显示出这种“间性”书写的特征,汉语作家在这方面其实也曾展开过各式各样的探索,比如对于文言语汇的巧妙借用。阿城和贾平凹等作家之所以能显示出自身所独有的个性创作风格,很大程度上就与他们对于语言的高度重视有关,而恰当地借用文言语汇即是展示其个性的途径之一。如: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阿城《棋王》)路遇一女子,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趋而前去搭话,女子闪进一家商店,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衣服钮扣错位,不禁乐而开笑。(贾平凹《笑口常开》)再比如,少数民族作家其自身民族的语言对汉语的渗透,以及不同地域的作家在方言写作方面的实践等。如:我想,汉人跟我们还是很像的。比如,一件不好的事,直接说出来,不好听,而且叫人难受,就换一个说法,一个好听的说法,一个可以不太触动神经的说法。他们不说我的叔叔给炸死了,死了,还连尸体都找不到了,而只是用轻轻巧巧的两个字:失踪。
可能正是因为这两个字的缘故,我没有感到多么痛苦,我对下人们说:“他把自己水葬了。”(阿来《尘埃落定》)乡长扭头去看县长的脸。县长脸上缺了表情呢,不知啥时候挂了蜡黄色,嘴角上有了一筋一丝的动,像他们说的啥话牵了他的心,像谁上前在县长脸上扯拽了一把呢。一瞬儿,县长把目光从四蛾儿头上漫过去,望着山那边一世界白,脸上的蜡黄又不知为啥淡落了。一脸膛都是平静了。(阎连科《受活》)电视台女记者激动的赞叹和围观人们钦佩的目光,仿佛只是年三十晚上放的一个小焰火,亮是蛮亮,熄得也太快。何汉晴想,狗日的,别人的热闹为么事那么长,我的热闹为么事这么短?(方方《出门寻死》)英国的语言学家罗宾斯认为:“在一种语言的范围内,文化阶级(通常也是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方言被当成是代表正确性的特定标准,而别的方言是未受教育的人所使用的变体或低级方言。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无视许多明显的事实,即非标准方言在不同的语言层面上保存着更古老的特征,这些特征曾经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一种语言中,只是现今在标准方言中缺失罢了。”无论是翻译语体,还是对古典汉语资源的发掘,抑或是对少数民族语言及不同地域方言的借用,这类书写基本上都是让“语言”处在了一种特定的“间性”书写状态。洪堡特认为:“在某种语法关系的表称不完全符合真正的语法形式概念的场合,往往便可见出一种语言的特定本性,……当语言开始迈出改进的步伐之日,也是人出于说话的物质目的不再对语言的形式属性视而不见之时,而这样一个阶段没有语言的作用与反作用是不可能达到的。”“间性”书写本身所蕴涵的就是一种“反向”的张力结构,其优势主要在于,一方面,它对于处在“惯性”状态的“普通话”书写会时刻保持必要的警觉,由此,在避免“普通话”写作所造成的所谓“流畅”的同时,“语言”本身将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适度的“阻隔”;同时,在另一方面,文本自身的这种“阻隔”也会迫使阅读者不得不减缓阅读的速度,以便不断地借助“回溯”来感知和体味“语言”自身所传达出来的“多向度信息”,“语言”载体的“丰满”因此也就成就了“文学”意味的“丰厚”。“语法关系的标记是由具体的、或多或少可分割的要素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事实,那么就可以说,讲话者与其说是在运用现存的形式,不如说是在每一瞬刻都自行构造着形式。语法形式由此往往就会变得丰富多样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寻找和创制“语言”的过程,实际正是创造“文学”的过程;当代汉语作家如果仍旧满足于现有的“普通话”写作范式,所谓的“汉语文学”恐怕真的会走向绝路。
顾彬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但对作家来说,语言应该是一切。恢复好的中文,也是中国作家的任务之一。……一个作家唯一的责任是语言。”应当说,他的这种诚恳而富有善意的提醒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承认,汉语在明晰而严谨地概括事物的表征等科学层面上的确并不具有优势,但是,惟其汉语自身所具有的含混、细腻、迂回和多义等人文特性更适宜于“文学”语言的需要,因而才成就了汉语“文学”曾经的辉煌和博大;汉语文学要想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和注目,回到语言本身以激发汉语所独有的活力,也许是当代中国作家所需要承担的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贺昌盛 单位:厦门大学 中文系
- 上一篇:生态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教育研究范文
- 下一篇:民间口传文学翻译的赫尔墨斯困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