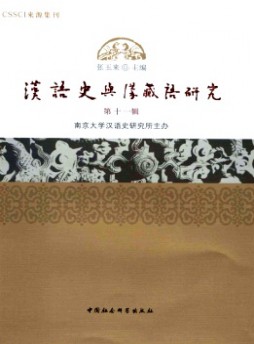汉语特点对汉语文学的影响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汉语特点对汉语文学的影响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研究”和运用语言。追本溯源地来看,一种文学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其所使用的语言。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相同。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字,总带着模子的色彩和线条。”①可以说,正是语言,在不同的文学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自然,本身极具特色的汉语在这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它潜移默化地从诸多方面的影响了汉语文学特色的形成。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那种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汉语的思维,带一种具象思维成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语是一种艺术性的民族语言,汉语思维具有艺术气质。这种艺术气质投射在文学上,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美轮美奂的中国文学。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典诗词受汉语特色的影响最深,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之一。它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为数众多的爱好者和学习者,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园地中一束光彩夺目的奇葩。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词入手,运用语言学相关知识,从艺术成因角度探讨汉语特征对汉语文学的一些影响。文字的象形与内涵的诗意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传承的,因而记录时所使用的符号即文字对于文学尤其是书面文学特色的形成影响至深。作为最基本的组成材料,汉字在潜移默化中以自己的特点影响了汉语文学的特色。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汉字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符号系统,它是一种表意性的象形文字。一般认为,认字的最早生成方式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四种。但若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无论哪种方式都包含了外指的“物相”和内指的“意向”两个因素,象形都是其基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可见,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标记来实现的;“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可见,会意是在原有的象形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揭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的;“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②。可见,形声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增加声符来扩大文字再生产的,即使是音译外来词,人们往往也喜欢为这些表音字加上音符,如“目宿”加“艹”成为“苜蓿”,“师子”加“犭”成为“狮子”,“皮离”加“王”成为“玻璃”等等。
显然,汉字是中国人习惯以直觉形象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致思途径的产物。在印欧语当中,假若你从未见过某一单词,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望其兴叹。而在汉语中,结果则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比如你可能不认识“獾”字,但透过左边简化后的形旁“犭”和右边的“”你总会猜到这该是一种读音近似“”的动物的名字吧。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汉字外形与内涵关系就是这么紧密。因而,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感于外而发于内”的心理意向,一种客体与主体的相互交融,一种经过概括化、模式化了的“共相”。汉字的这种构成体现了主体对于客体的感觉、体验与选择,颇具诗的意味和审美的意味,因而也更适宜于抒情写意,从而促进了中国诗词艺术的兴旺发达。日本学者儿岛献者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而指事会意形声皆有一部分之象形,象形与图画,只有精粗之异耳。试观郭璞《江赋》,通篇文字于纸上。再观司马相如之《上林赋》,篇中叙山者崇峨崔嵬崭岩崎岖等等,皆冠以山,叙鱼鸟者亦如此,皆冠以鱼鸟之偏旁,山与鱼鸟皆象形也;故一篇文字全体生动,善写高山绝峰,峻极于天之雄势,易使人想见鸟飞天鱼跃渊之活境,皆于文字构造有图画性质之所致。”③可是,汉字在不断地演化过程中,流失了许多感性的东西,导致图画性和意象性不断减弱。现代人欣赏到的用简化汉字记录的中国古典诗词已较它们初被记录下来时逊色得多。但由于长期的、历史的文化心理积淀,汉字的这种“诗性”的特征在诗词哲学过程中往往从潜意识的深层弥漫开来,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诗的含蓄,韵的浑融,气的烟蕴。比如“暮”与“晚”,意义相同,韵味大不一样,观其原因,还是和“暮”字的形义、渊源有关,“暮”的原字即“莫”,而“莫”的初始写法则为“”,即日落草莽之中,因而“暮”比“晚”更能体现出雄浑苍茫之象。如“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李清照《永遇乐》)。
正因为汉字是这样一种脱胎于图画的文字,是基于主体对于客体的直感的、形象的、整体的把握,而不是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规定之上,因而汉语词汇的意义往往是浑然而模糊的,具有独特的“观物取象”的功能。它往往是一种整体象征,所突出的并不是客体的确切属性,而多半是主体“心理形象”。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希腊的“月亮”(men)指的是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意义,而拉丁语的“月亮”(Luna,Luc-na)则是指月亮的“亮度”。我们可以加上汉语的“月”比较一下,“月”显然是取月亮在常态下的“形状”的,比起“时间”和“亮度”来,“形状”显然直观,却少有思维的规定性、单一性、明晰性。“月”中似乎什么都包括了,然而又都没有说清。至于后来的诗词作品中,又把“月”称作“玉钩”(“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李贺《七夕》)、“桂魄”(“桂魄初升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王维《秋夜曲》)、“寒蟾”(“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李贺《梦天》)、“银蟾”(“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毛文锡《临江仙》)、“清辉”(“多情别,清辉无东,暂圆常缺”———王微《忆秦娥》)、“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等,就更加感觉化,富于整体象征,也更加模糊朦胧如梦境幻境了。这样的文字,缺乏科学语言所要求的透明度,但却更加适合表现诗词中文学性艺术性的意象。汉字自产生之日起,就为汉语文学准备了相当富于诗意内涵的基本的材料,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提供了相当适宜的生长土壤。音节的特点与形式的构建中国古典诗词表象的特点是形式整齐,同时,这也是艺术形式的特色之一。它的引人入胜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擅长带着脚镣跳舞,四言、五言、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的种种要求及品目繁多的词牌规定,已经注定中国古典诗词是严守纪律的一族。它们看上去井然有序,读起来琅琅上口,颇具形式之美,音乐之美,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性。而这一切的成因,都与汉语音节的特点密不可分。
不同于印欧语以音系作为基本的语言感知单位,汉语的基本感知单位是音节。音节由声母和韵母构成,声调则把它们紧紧包裹住,因此,汉语的音节非常整齐,切分明确,在书面上则有一个个方块汉字与之相对应。汉语的这个特点不仅使汉语能在形式上作十分整齐的排列,而且为汉语文学中的对仗、对偶等手法的运用与工整的形式安排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基础。中国古典诗词便充分利用了这一基础,对仗、对偶在篇章中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成为一种要求,如律诗要求颔联、颈联中的上下两句相对,一些词牌中作出了关于对仗的规定等,而且在长久的写作中,诗人们还摸索出借对(即利用一字多义的现象以构成对仗。一个字有甲、乙、丙等多种意义,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借用它的乙义或丙义与另一字相对。例如杜甫《曲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流水对(即一联中的两句字面是对仗的,意思却是相承的。例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等特殊对仗法,增强了艺术审美效果,颇值得玩味。如果说音节的组合为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诗)的格律树立了基本梁柱的话,那么音节的声调变化则使梁柱成为“雕梁画柱”,前者奠定了节奏的基础,后者以平仄的变化配合造成音调的和谐。在汉语里,每一个单音节的字都有一个声调,来反映音节高低升降的变化。声调最早发见于南朝的齐梁之间,有下上去入四种,其中上去入三种声调统为仄声,与前面的平声相对。在此之后,文人们在诗词创作中开始利用汉语四声的特点,有意造成声韵上的平仄相间变化,读起来抑扬顿挫,天然具有一种音乐美。
让我们以刘禹锡的《酬尔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和陆游的《鹧鸪天》为例,来看这种音韵上的平仄变化造成的音乐美感。刘诗如下: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诗中字的平仄为: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陆词如下: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啸傲,看蓑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词中用学的平仄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相反,一篇作品即使意境再美,如果在音律上发生非和谐现象,审美意识与情趣将大受损害。且看下面语音的趋同性例子:屋北鹿独宿(全仄)溪西鸡齐啼(全平)中国古典诗词一方面将其声律模式建立在汉语单音节和四声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在汉语单音节声韵配合的特点上建立起具体作品的音律形象④,以独具一格的音响审美效果传达作品丰富的思想感情,大大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古代韵书里,凡韵腹和韵尾相同的字,就归为一个韵,《广韵》中有二百零六韵,古代韵母系统之复杂可见一斑。韵的数目如此繁多,每个韵训都为诗人潜心揣摩,不同的韵部产生了不同的情绪效果。宋人把《广韵》中的二百零六韵分成十六撮: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每一摄对古典诗词作者来说,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体验,这种体验往往是下意识的,但确是区分得非常明确的,请看下面的四首诗词: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花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重重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韵脚:州、由、愁、头,押流摄尤韵。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鬃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韵脚:侯、州、裘、秋、流、洲,押流摄尤韵。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韵脚:荒、茫、墙、肠、乡,押宕摄阳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活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韵脚:茫、量、忘、凉、霜、乡、窗、妆、行、冈,押宕摄阳韵。四首诗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中都有悲愁的成份,但前两者是忧愁凄怆的味道更浓一些,后两者则在悲伤中流露出一丝阳刚之美,之所以如此,和韵的选择关系密切。不同的韵有不同的美学价值,这可能和韵母的音色有关。韵脚就如乐曲的主音,主音决定了一首曲子的调性。汉民族的诗歌,不仅在于意象、气韵,还在于音乐感。所以刘勰说:“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⑤气力的强弱、刚柔就在于和谐与押韵。正因为汉语言在语言单位组合方面具有美的极大潜力,历代诗词作者无不醉心于语言的编排与操练,留下了大量具有语言形式美感的文学作品。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看重形式之美。可以说,正是由于古人在创作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与毅力,才使语言形式上的切磋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竞技保留项目。启功先生曾引张裕钊与吴汝纶论学手札说:“昔诸子谓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著式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⑥
经过众多文人许多年的努力,汉语文学的形式已经被造得十分精美。由于语言发展的连续性,古人作诗填词时“用破一生心”营造出的许多美妙形式,仍有一部分保留在现代汉语里,继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习惯语和成语当中,这种例子更是常见。这使人们在不经意间便领略到了那种形式之美,如“折戟沉沙”、“落花流水”等词汇本身,给予我们的即是一种享受。更有甚者,这种重视形式的传统已经形成了一种无竟识,因而在中国,即使是在店铺茶馆的外面,也常常看到“对联”高悬,如“和气远招十一利,公平广进四方财”,“坐片刻不分你我,喝一碗各奔东西”,不能不说这种无意识影响到了文学家的创作。可以说,汉语音节的特点及在此基础形成的声调及韵的划分,赋予了汉语文学与众不同的魅力。语法的特点与潜力的开掘这里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李白的《静夜思》与其英文翻译:原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译文:Sobrightagleamonthefootofmybed———CouldtherehavebeenafrostalreadyLiftingmyselftolookIfounditwasmoonlightSinkingbackagainIthoughtofhome不难发现,在译文中,原文里未加确定的时态和人称都被一一落实,诗中本来可以想象补充的空白荡然无存。同时found、thought等词的使用把本来连续的动作变为终止性的行为,原诗幽远的意境也消失贻尽,从而也便失去了中国文学那种特有的模糊之美。这不仅是《静夜思》一首诗在翻译时面临的尴尬,而且是绝大多数中国古典诗词在译成印欧语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里,最高明的翻译家也难以再现原作之美。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汉语语法的特点关系密切。汉语是一种分析语,具有极端的分析性,这使得词语的组合十分方便,不受形态的约束,没有印欧语那种复杂的形态变化,不像后者那样在数、格、时态、语态和词性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汉语的组合主要靠语义和语序,词和词之间没有绝对的排斥性,只要语义上合乎逻辑事理,就可以搭配。所以,汉语的组织往往是语义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考虑大于句法的考虑。这种组合关系常常能够容忍许多从逻辑上看是非常奇怪的组合。在这种宽式语言中,作家就如同在大海中游荡,自由地表现自己,随心所欲,畅所欲言。请看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三句,是晚秋游子感情的自然流露,无一动词,全是双音节名词有节奏的铺排,流畅自如。再看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歌声怎么“踏”?英语中恐怕非得用“With”来介绍“歌声”,汉语没有格的限制,“踏”和“歌声”通过意义自然连接,不牵强附会,解释成“在歌声中踏行”,就是踏着歌声!这是语言和感觉融为一体的彻悟,欢快、喜悦、节奏、歌声聚在一起。李白还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的妙语,“半落青天外”、“中分白鹭洲”和“踏歌声”用法相同,是诗人、语言、景物的自然融合。柳宗元《江雪》中的“独钓寒江雪”,正是汉语赐给诗人的想象境地。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必得用“in”引入处所格“雪”,对于汉语来说,把“寒江雪”当处所还是对象,可以自由想象。
很多学者都认为,汉语语词组合自由,使汉语免除了许多规矩,与意象组合无关的成分都可以省去,因此汉语的表达往往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由于汉语的单词蕴藏了丰富的语文感受,因此将这些基本粒子排列组合起来,就成为一组组生动可感的具象。中国的文学语言大师们在采用这种具象思维的语言时,也大都用具象的手法来捕捉事物的形态,描绘心中的感受,这往往能触发每个经过中国文化熏陶的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当一个个语词的具象被诗人艺术地精心安排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内涵的丰富联想和民族情感就组成了连续的有机的画面,未着一个动词,而动作自在其中;未用一字抒情,而心境溢于言表,因而发散出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将一首中国诗译成英语,要作许多处理,要增加许多元素(如动词的变化,单复数,冠词等等),但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并非都要这样,反而倒是以不作这种处理为佳,诗的印象仍旧完整无缺,而作了那些处理,诗却会受损。中国古典诗词所用的文言,由于超脱了呆板分析性的文法语法而获得更完全的表达,如唐代陆龟蒙有这样一首七律:平波落月吟闲景,暗幌浮烟思起人。清露晓重花谢半,远风微动蕙抽新。
城荒上处樵童小,石藓分来宿鹭驯。晴寺野寻同去好,古碑苔字细书匀。该诗也可以倒过来读:匀书细字苔碑古,好去同寻野寺晴。驯鹭宿来分藓石,小童樵处上荒城。新抽蕙动微风远,半谢花重晓露清。人起思烟浮幌暗,景闲吟月落波平。读者丝毫不觉得语法有何不自然,西文要同样做,却根本不行。原因就在于西文无法使一个字母同时兼有两三种文法用途,而不需要字面上的变化。西文的细分限指特指的要求,使它无法可似中国文言这般自由。中国古典诗词文法语法上的自由,意味着其欲利用语字的多元性来保持美感印象的完全。试看杜审言诗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⑦如果像下面译诗中那样加入一些连接元素,译成:Cloudsandmistsmoveouttotheseaofdawn.Plumsandwillowsacrosstheriverbloominspring.或者解说为:“云霞从海上映出一片曙光,梅柳渡过江带来一派春意”。这两种方式显然都歪曲了原诗的美感印象的层次和姿态。文言是没有时态变化的。没有时态变化就是不要把诗中的经验限指在一特定的时空———或者应该说,在中国诗人、词人的意识中,要表达的经验是恒常的,所以,不应把它狭限于某一特定的时空里。印欧语系中的“现在、过去、将来”的时态变化就是特定的时空。汉语文言中的动词类字眼,可以使我们更接近于浑然不分主客的存在现象本身,存在现象是不限于特定的时空的。词法上的宽泛同时也造成了词的“多元性”,如在“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黑”中,“白”“黑”二字既可理解为动词,又可理解为形容词,因其兼具活动及状态两种不可分的情况。同样,“青山横北郭”的“横”字既是动词亦是前置词。词的“多元性”在翻译上会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词性的限制,译者必须作出种种处理决定,而限制了原诗的多面延展性,直接破坏了原诗的美感活动的程序和印象。
总之,汉语是轻形态而重功能的语言,这使它在词法与句法上都没有许多限制,进入这种语言框架中的现实不需要经过多方面的界定,因而现实本身也就不必清晰地多方面呈现自己的特征,所以说,汉语更适合作为艺术文学的载体。王力先生曾经说过:“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⑧所谓“法治”,便是讲规律,讲逻辑,讲严谨,讲精确;所谓“人治”,便是讲直觉,讲感悟,讲意会,讲传神。“人治”的特点增强了汉语言的人文精神,提高了言语主体在言语实践中的自由度,为主体意识的自由驰骋,为言语意象的自由组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学。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 上一篇:水费征收和水资源监管通知范文
- 下一篇: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意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