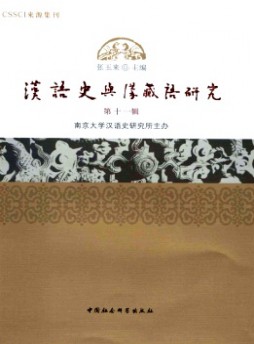汉语文学语词的艺术化组合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汉语文学语词的艺术化组合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汉语是一种充满诗性资质和审美表现性的语言,它的组合主要是依靠词序排列和虚词的应用,词本身的形态则大多不变。如“我爱他”,换成“他爱我”,语义便翻转了,而语义的变化只靠“他”和“我”的位置颠倒;如果加上一个虚词“也”,就可使两个句子的意思统一起来,成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即“我爱他,他也爱我”,这就由两个单句构成了一个复句。可见,语序在汉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语言受线性序列的限制,一个语词不得不排列在另一个语词的后面,但它们之间可以前后移动、相互置换,在形式上具有可逆性。“汉语言单位的弹性表现在功能上就是它的变性,亦即词义功能的发散性。汉语一个个词像一个个具有多面功能的螺丝钉,可以左转右转,以达意为主。只要语义上配搭,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连在一起,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1]正是汉语的这种随意性和弹性,决定了语词组合的多向性。“一个语词序列,可以顺向建构,也可以逆向拼合,还可以以腹为头双向合成。”“语句可以无限延伸,语序可以随意调整,语链还可以自由地切分。”[2]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充分利用汉语语句结构之灵活多变的特性,通过语词艺术化的组构,成功地表现着审美意象和艺术境界,传递着美的信息。汉语文学文本中的语词组构策略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仅从下面五个方面便能看出汉文学语言建构的特点:
一、运用表象义丰富的词,复苏语言与感知觉表象的潜在联系
语言是由语词构成的,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所以,语言这种抽象化、概念化的符号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尽管如此,语言仍与人的感知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既有普通一般的一面,又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因为语词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语词与表象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房屋”这个词,它虽然指的是许许多多房子的抽象,但它又始终是与个别的房子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在理解这个词的时候,在把握共义的前提下,又都各有不同。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理解不一样,大人与小孩的理解不一样,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不一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解不一样,因为他们理解这个词所依据的生活经验不一样。这就说明,“房屋”虽然是一个共义性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完全割断与个别事物的联系,在向人们显示它抽象普遍的一面的同时,它也向人们显示出其具象特殊的一面。由此可以推见,语词的意义准确地说应分为意义和涵义两部分,意义与抽象认知有关,是普遍的、分析的,而涵义跟感觉有关,跟过去的经验、文化背景有关。意义可以传授,涵义只能靠语境、语感去领悟。现代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划分愈趋精细,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就把语义分为七类:理性义、内涵义、社会义、情感义、反映义、搭配义、主题义。[3]这说明语词语音层面下面的语义呈现出一团“意义星云”,以理性义为中心,周围弥漫着诸多模糊不清的边缘义。词义的多向性与弹性为文学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文学是用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主体情感的,形象性是文学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在文学语体中,比较重要的是语词的表象义、情感义、社会文化义等,这些边缘义间互相联系,且都以“联想意义”来概括,能引发巨大的表现潜力和暗示力。表象义是词的所指对象在我们脑中引起的感知觉表象,通过表象可产生联想,唤起相应的审美情感。因而表象义在文学语言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作家倾向于选择表象义丰富的词,以使意象得以形象地符号化。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古道”、“西风”等都是表象义凸现、鲜明的名词,这些词能引发人们对所指客观事物的联想,能在头脑中建立起相应的感性的画面。以这些词作为语言材料,经过诗人精心地组合建构,便形成了一首形象生动、意蕴隽永的“秋”的千古绝唱:“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普遍一般性的语词,经过诗人的具体化组合,使之指向了具体、特殊的事物,唤起人们的感官具象反应。诗中每三个语词为一组,分别构成三幅看似独立的图景,但其中都蕴含着一个悲凉的主题。各个语词所标志的事物的状态,由近及远,由静及动,由次及主,由外到内地分层推进、立体延伸;景色的描写与心理的衬托相得益彰,每一个自然景物中都渗透了萧条秋色里人物内心世界的悲凉。
二、利用词义聚合的不同特性,造成有意味的文学话语
汉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在《汉语大词典》中就收集了37万多条(只包括一般语词)。同一事物常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或名称,例如,“死”历来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尽可能用委婉的说法来表示:“仙逝”、“谢世”、“永别”、“长眠”、“归西”、“作古”等等,有多达几十种说法。这些语音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就是一般所说的同义词。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巧用语言系统中的同义词不仅避免了用词的重复,为句子带来错综变化之妙,而且能通过运用同中有异的同义词,传达出不同的情感色彩和风格色彩。如《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贾府衰亡的过程,全书贯穿着悲和愁。为了表达各种场合、各类人物、不同程度、不同内涵的“悲”和“愁”,作者运用的两组同义词共达36个。其中表示因悲而痛的有:“悲痛、悲恸、悲切、悲凄、悲戚、悲哀、悲”;表示因伤而悲的有:“伤感、伤心、悲感、悲伤、伤悲”;表示凄苦的有:“凄楚、凄恻”。愁有感于形而虑的“烦虑、忧虑、愁烦、忧愁、忧”;有动于心而闷的“愁闷、忧闷、纳闷、气闷、烦闷、闷”;有心绪不展的“悒郁、忧郁、抑郁”;有心境不畅的“懑愤、懊恼、烦恼、苦恼”。笔之所至,无所不及。于贾府,则愈显出封建社会摇摇欲坠之态;于宝黛,则更见其愁肠固结,如泣如诉。[4]在语词的意义聚合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语词的多义性,即通常所说的一词多义现象。例如,“蜡烛”一词的实体词汇意义是“蜡制的照明物”。以这一实体词义为基础,又生发出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国俗语义。以燃成灰烬始干的烛泪喻深深的情思和虽死不悔的决心和信念;根据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质,“蜡烛”一词用来泛指“乐做奉献的人”,特指“教师”;由于摇摇曳曳的烛光易被风吹灭,又有了“风烛”比“残年”的用法;中国过去在婚礼中,在新房内以点红蜡烛表示喜庆,并于红烛之上加上龙凤彩饰,以增添吉祥热闹的气氛,是为“花烛”。“花烛”遂指代“新婚”,“洞房花烛夜”即为“新婚之夜”;而在“他是蜡烛,不点不亮”这句话中,“蜡烛”一词具有贬义,泛指“不自觉、有傻气的人”。可见,“蜡烛”一词具有丰富的象征义、比喻义,修辞上有褒有贬,既表现缠绵之情,欢乐之感,也表现悲凉之意。这种种丰富的涵义都是在“蜡烛”一词的实体词义的基础上所增添的民族文化蕴含,是通过对蜡烛实体的特点的联想而产生的。一词多义现象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它使语言非常经济,一个词包含几个意义,可以大大减少语言符号的数目,使用者能从词汇所具有的涵义的汇集中,获得无比丰富的意义,并可以根据上下文选择出一个与表达目的最为吻合、恰当的涵义。消极的一面在于易使话语产生歧义现象。正因为如此,对于一词多义,人们在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中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科学语言中,不允许存在含混不清的表达,要力求消除语言的多义现象,使语词的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而文学要用语言表达出作者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原初的审美感受与体验,意义明确单一的语词是难以传达出如此丰富复杂的审美体验,因此,文学语言就要提倡和保留语词的多义,并通过各种手段造成一词多义现象。正如法国释义学派创始人保罗•利科所说:“诗歌是这样一种语言手段,其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筛去或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不再是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构建单独一种意义系统,而是同时构建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同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5]文学语言恰是善于运用语词多义性的语言,利用同一语词具有的多种意义,拓展了文学作品的容量和内涵,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明天。”(杜紫微《别诗》)这两首诗中都以垂泪的蜡烛象征苦恋者那黯然销魂的离别之恨和幽然神伤的思念之情。而在“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蜡烛!”(陆文夫《井》)中的“蜡烛”一词则是贬斥性的骂语,意思是“什么东西,那么不自量!”正是由于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的特点,因而才能够包容众多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和哲理意蕴,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表达效果。
三、创造语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偏离效应”,使一般化语词生发出独特的表意功能
在日常语言中,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对应关系,即使一词多义,也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语词的常态意义。这些常态意义的表现性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它要受到语法规则和造句习惯的制约,语言表达难以脱离概念化的逻辑轨道。相对于理性逻辑,艺术形象中的生活与情感则是变异了的。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节夫在给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作序时深刻指出:“情感、情绪和激情是艺术作品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作品中是经过改造的。就像艺术手法造成作品材料的变形一样,艺术手法也造成情感的变形。”[6]这就告诉我们艺术作品中的情感是个人情感的改造与升华,要成功地传达这种变异的情感,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与手法,就要在日常语体的基础上转换生成审美语体,其转换生成的基本规律是:“只有违反标准语言的常规并且是有系统地进行违反,人们才有可能用语言写出诗来。”[7]在实际语境中,词义又是变化多端的。当词义的变化超出语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确定联系时,能指与所指间的恒定关系就会破裂,偏离也就随之产生。偏离的另一层意思便是指在词的用法、搭配及语法功能等方面违背常规的用法。语词的偏离在两个方面造成独特的表意效应:首先,通过言语的偏离及超常搭配,打破其常态,使语词不再指向共相、一般的意义,而是指向独特、个别的意义,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如“花”这个词,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对它的解释多达19项,其中包括“花”的一些比喻义、象征义,但是,这些解释里“花”依然是共相意义上的“花”,能指与所指还是能够确定的。在文学作品中,采用偏离的方法及语词的超常搭配,“花”便指向各种特殊的事物和意义,“花”的意义和用法是变化万千、无法穷尽的。诗人张先的佳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被视为千古绝唱。“花”本来是不能“弄影”的,但恰是用了一个拟人化的“弄”字,而境界全出。这是诗人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到花上,使花人格化的结果。在月光下徘徊、起舞、顾影、伤愁的既是花也是人,是二者的巧妙融合,是物化了的诗人的审美感受。没有“弄”字这一超常搭配的语词,则花归花,人归人,诗人的心境无法窥见,花的出现也失去了意义。显然,这一佳句中的“花”,不可能是共相意义上的花,而是殊相意义上的,即诗人独特情感体验中的花。其次,语词的偏离能恢复语言感性鲜活的表现力,并打破读者心中固有的接受定势。语词的常态意义由于经常使用,已变得机械化、一般化了,既失去了它与感性经验的联系,又使人在接受过程中感觉不到其生动鲜活的一面。文学语言通过言语的偏离和打破其成规与常态的“变异”,能够使人们产生新异感,并有助于打破那种非艺术接受机制的惯性运动,产生出艺术语体所需要的言语接受图式。譬如,我国古典诗词中对“愁”的描写,总是用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来表达这种抽象的、飘忽不定的情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有长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重量;“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愁有形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愁能相对而望;“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言还慵。”———愁有酒味,能醉人;“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愁有动作,能陡然立起。这里,诗人将难言的愁思,别出心裁地用文字凝铸成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意象,令读者在曲折玩味中觅得诗词的真谛。这些诗句中对于语言常态的偏离和“变异”的表达,迫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语言本身,而不是它以外的别的东西。新异、独特的语词搭配,使我们感受它时已无法重复原来的感知路径,无法袭用原来的接受模式和套路,只有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悉心地去体味、感悟。这就打破了我们心中原有的接受定势,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惊醒起来,使思维恢复生机与活力。颠倒词序,在语言方面设置一些“谬误”和“悖理”的现象,在诗、词、曲、赋中常能见到。如南朝江淹的《别赋》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全赋论及各种离情别绪萦绕心头,牵肠搅肚,使人痛苦万分。但言“心折骨惊”,论理上是不通的:人的心灵怎能折断,无感知的骨头又怎会产生惊惧之感呢?显然,这是作者对正常词序的有意颠倒,旨在强调离愁使人的心灵如同猝然折断破碎,这种愁怨竟然使无知的骨头都为之震惊,那么其痛苦程度不就可想而知了吗?若按正常词序“心惊骨折”,则失之泛泛。为了使言语表达简练形象、生动活泼,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词性,在文学作品里运用得也很普遍。如“雨丝斜打在玻璃窗和水泥窗台上,溅起的迷茫将窗外的世界涂染成一幅朦朦胧胧的图画。”(张建文、高立林《为了国家利益》)把形容词“迷茫”活用为名词,表示颜色,形象生动,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
四、“碎片化”的语词组合,拓展文本内在的艺术张力
文学文本的话语结构从本质上说是作家在观照生活时审美情感秩序的外化。就是说,一定的审美情感模式必然会产生与其对应的话语结构。正如杜夫海纳所说:“艺术的语言并不真正是语言,它不断地发明自己的句法。它是自然的,因为它对自身说来就是它自己的必然性,一个存在的必然性的表现。”[8]作家在创作中要以自己活跃的审美情感去超越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语法规则,同时就需要建构出能满足非理性思维的要求,能充分反映作家审美情感和创作个性的新的语法规则,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充分满足了这些要求。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可按其规则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而产生出不同的语句和语义,而且趋向无穷。这一语法理论是以既有的语法规则为前提,强调语言运用的变化性、创造性,它允许对旧有的语法进行破坏、改革,以便通过语言形式的重组来生成新的语义。这种转换生成法是符合文学语言组构规律的。作家如果遵循现象之间的因果必然律,按照常规语法去反映现实、组构文本,就会把生活中许多偶然的、个别的、无法按照因果关系去解释的意象与思绪筛选掉、遗漏掉,使文本的面目变得苍白虚假。为了突破旧有的话语结构模式,一些作家在结构作品时不仅选择了片断拼接的结构形态,而且大胆采用“碎片化”的语词组合方式,以使那些无法贯穿于因果关系链上的大量偶然的、个别的意象都被拼接黏合而纳入文本世界之中,形成散点透视的效应,使意象之间的范围、距离、深度增大,拓展了文本内在的艺术张力,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如巴金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没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纯洁的初恋,信托的心,白首的约,不辞的别,月夜的骤雨,深刻的心的创痛,无爱的婚姻,丈夫的欺骗与犯罪,自杀与名誉,社会的误解,兄弟的责难和仇视,孀妇的生活,永久的秘密,异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乡,兄弟的死,终身的遗恨。这段是在叙述一部电影的情节,它是由18个偏正词组并列拼接而成,其中有的词组内还含有并列着的多个信息。每个词组都是一个独立的意象,多项词组聚合成动态的意象群,各项之间看似没有必然的联系,显得零乱杂多。但却在广阔的时空中延展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貌似零乱无序的语词搭配中,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和各种复杂的情感。
五、营造各种特定的语境,使语词获得具体、特殊的涵义
由于文学语言的运用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并受特定语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文学文本中的语词不仅具有它本身的词典意义,而且还包含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形成的涵义,“词既是能指的又是表现的。说它是能指的,是指它含有一种客观意义,这种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它的外部,要求运用理解力;说它是表现的,是指它本身含有一种内在意义,这种意义超出了理解力所把握的客观意义。词是符号,又不只是符号:词陈述,同时又显示,而它显示的与它陈述的并不一样。”[9]这种内在意义(涵义)之所以与意义不同,就因为它是由生活产生的,它所反映的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对于语词内容的一种主观体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言外之意”,它潜藏在符码形式的深层。所谓语境是指使用语言时所处的实际环境,即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语境在范围上有大与小之分,在形态上则有显与隐之别。小语境指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后语所形成的言语环境。大语境是指语言表达时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小语境是易被人们注意的显语境,而由言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所构筑的大语境,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隐语境。由于文学语言的运用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并受特定语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文学文本中的语词不仅具有它本身的词典意义,而且还包含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形成的涵义。同样一个陈述事实(语言),在不同的陈述情况(语境)里,便会具有大相径庭的功能效应。正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普通语词才能生发出具体的、特定的意义。如“老爷”一词是普通的旧式称谓,虽然显示着封建等级关系,却没有丰富、深刻的涵义。但是,在鲁迅小说《故乡》的特定语境中,“老爷”一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味。童年时,“我”与润土是亲密无间、无所顾忌的伙伴。时隔30年,润土见到我却恭敬地称我为“老爷”,这生分、隔膜的称呼,不仅表现出润土对“我”的尊敬,而且折射出了他那自卑、麻木的心态,包含着既欢喜又悲凉的情感,显示着人与人之间无法突破的隔膜。在此,语词不止诉说着自身,它说出了远比自身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的涵义。可见,在具体文学语境下,一句普通的话语可生发出无比丰富的涵义,令人品味不尽。这正如美国著名的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的:“事实上,语词在不同的前后关联、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都具有不同的内涵。”[10]由语言的上下文关系构筑的小语境,容易被人注意和引起重视,而言语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习俗等)造就的大语境,常被人所忽略,其实,恰是这些隐而不见的社会文化因素,是形成文学语言深层涵义的根本原因。如杜甫的《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足,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该诗描写了一只离群的孤雁不饮不啄,一直苦苦地追寻着失散的伙伴,甚至产生出那群雁总在眼前晃动的幻觉;但这幻觉毕竟不是真实的情景。在它周围“鸣噪”着的并不是昔日的伙伴,而是一群可恶的“野鸦”,这只孤雁因此而愈加焦躁不安。表面看来,正如题目所表明的是一首描写孤雁的诗,实际上它是诗人的“自写照”,即借用孤雁这一动物形象抒发对知己的思念之情和对因战乱带来的人与人之间那种不信任现象的诅咒。诗中借孤雁这一象征体所传达出的象征意义(内涵意义)是非常丰富、深刻的。而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诗句中内蕴的涵义,则要联系大语境,即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理解。语境赋予语言以个性化涵义和生命的活力。正是在一定语境的规定和限制之下,抽象概括的语言符号才变得具体、生动、形象、丰富,从而转化成情味无穷的艺术符号,作家运用这样的艺术符号,才能创造出内涵丰富、诗味隽永的艺术形象。所以,在文学作品里,词语的意义是从作品的整个话语系统(大语境)中获得的。因此,一些词语不仅具有表意功能,而且具有传递审美情感的表现功能,单纯的语言符号已转化成艺术审美符号。文学语言与作品中的具体情境紧密相连,文学语言正是在语与境这种唇齿相依的文本结构中获得了它的审美性。总之,文学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并非是语言学中的语言,而是超越了普通语言规范的变异的语言,是作家心灵创造和审美组构的结果。在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信息和情感内蕴,它能成功地呈现出作家心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和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