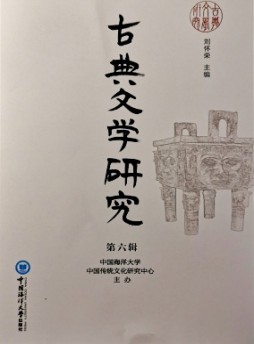古典心灵与现代意向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古典心灵与现代意向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正如安徽青年作家赵焰所言,他的小说都是他用心打磨的一粒粒珍珠。在这些珍珠中,我们可以窥见世纪之交一幅幅清朗的人生图景,弥漫其中的温情在一片喧嚣的欲望轰鸣中更显珍贵。《春晓》讲述了一个卖了自己的居所承包荒山的男人,妻子无法忍受荒凉后弃他而去。逃婚的女人就是在这个大雪封山的黄昏走入了他的视野,融入了他的生活。小说截取了平凡的“他”和女人之间极普通的人生片段,并将这种人生的片段和特定的自然环境及心理活动进行了艺术的糅合。《冬日平常事》在赵焰的笔下文静淡雅,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天光和村里的俏姑娘相爱,但老六头怕因此失去儿子,反对儿子的亲事;儿子因此变得沉默,老六头最终撮合了儿子和俏姑娘的亲事。这的确是冬日里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与《冬日平常事》类似的还有《叟》、《冬天里的斜阳》,这两篇小说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将叟与同院的夫妇及其小孩之间、小青和他的作家男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娓娓道来,跃然纸上。美好的情愫与作家敏感的心灵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主客体交融的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磁场。
进一步深究,我们发现赵焰并没有满足于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描摹。在我看来展示和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并与之进行深层次的对话才是赵焰叙述清朗的人生图景的内在动机。以一种平民视角,真正体悟生命中令人感动的成分。这种感动的成分也许并不在于他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不局限于他的身份。构成芸芸众生主体的老艄公们的举手投足、内心的微波都因为心灵的浸润而具有了感动人心的内在气质。在我们平凡的人生中,这样的生存方式具有普遍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与之进行心灵的交流要比不切实际的启蒙要有意义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英雄史诗是必要的,但揭开被史诗所遮蔽的人类的心灵史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温馨的青春气息
关注人的成长之痛是赵焰小说的另一个支点。在赵焰的笔下,少年情怀具有别样的人生况味和文化心理内涵。
中篇小说《晨露》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交替的手法展开叙事,以内聚焦和外聚焦两种视角拓展叙事空间,在视角转换和人称变换中,10岁男孩“我”对23岁的英俊青年玉的纯真情感得到了立体的展现,并由此打通少年和成年人之间心灵的通道。尽管一切人对于“我”与玉的交往不能理解,但“我”无暇顾及,因为“我”单调而苦涩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的孩童世界因此阳光普照。玉的坠崖身亡,使“我”,“一个经受精神痛苦的情感折磨的男孩在涅粲的升华中重新复活”。值得注意的是在《晨露》中,作家在少年和成人的双重视角中审视了死亡这个人类生存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玉死后,“我”的童年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童年的载体,“我”晶莹剔透的少年情怀正是在“玉”中折射。在“玉”碎后,每一块碎片都烙上了“我”生命的印记。赵焰的这种生死观显然已经具备了哲学的意味:“对死的畏惧从反面促进对生的动力,它意味着人将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来积极筹划有限的人生。”①
中篇小说《栀子花开漫天香》讲述的是中学生憨儿与借读到乡村的“美丽绝伦”的城里姑娘杨柳之间的故事。虽然杨柳最后离开了乡村,但她的气息就如那漫天盛开的栀子花,香味已经沉淀到憨儿的血液里。这种朦胧但却美妙的情绪在憨儿的内心生根发芽。在《秋天里的斜阳中》,男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情愫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甚至在已经功成名就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切繁华与荣耀都已经成为虚空,而儿时女孩的一颦一笑竟然成为男主人公生命终结前最珍贵的回忆。赵焰以艺术家的敏感和良知在小说中与这样的玻璃心进行真诚的对话,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熨平了我们淤积于心的“折皱”。
成长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存在状态,少年必须经过不断成长实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逐步走向实现自我的未来人生。在这个过程中,生理与心理都在试图超越,并被文化、社会等后天因素填充,从而达到生命状态的新的平衡或裂隙。赵焰的小说曲径探幽,深入到少年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微妙而丰富的心灵颤动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此基础上,赵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种成长之痛在人性中的沉淀、发酵,成为生命底色的事实。青春的底色虽然略显暗淡,但由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强势介入而显得刚健清新。在喧嚣的新时期文坛,赵焰表现出如此浓厚的“青春情结”,我以为这是作家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现代性建构的基础无疑是人性的完善。人性不是一句空谈,它体现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青春期的人性具有阳刚之美,与靡靡之音构成强烈的对比,它实际上对应的是赵焰心目中理想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哲学模式,一种走出精神困境的方式——这种阳刚之气或许可以与阴性的古老的徽州文化形成互补。
幽远的徽州故道
赵焰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他的小说无一例外地以徽州为背景,小说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徽州文化的烙印。
实际上,面对徽州,赵焰是陷入了一种理性与情感的两难境地的。一方面,对于故乡徽州他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他以舒缓的笔调用心素描徽州。这个时候,徽州已经打上了赵焰情感的烙印。赵焰关注的是徽州的自然山水,他认为徽州人的舒缓从容平淡的生存状态与山水灵性是相通的,这样的诗意人生反映了徽州文化的诗性特质。这种诗意生活无疑是赵焰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在小王老师与刘桂兰(《遥远的绘画》)的眼里,徽州的乡村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就连武林高手一流剑客林荒原(《美剑》)也惊异于黄山的绝世美景。我们看到,在赵焰的眼里,徽州文化的自然品性更为迷人,因为是自然而不是具象的牌坊等培养了徽州文化的性格。社会的变迁可以损毁具象的建筑,但奠基于自然山水之上的徽州文化精神却可以穿越历史的局限在徽州人的心里开花结果,也奠定了徽州人的韧性和超强的生存能力。
但赵焰借助徽州山水所表现出的理想生存状态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徽州地处中华腹地,绵延的山脉环绕着局部的秀水。大山的环抱成了抵御外来文化干扰的天然屏障,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场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主宰着人们对生命与世界的看法。在这种内向型的文化生存圈中生活的人们对外来文化有着近乎固执的排他性,它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徽州文化的内在延续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徽州文化的文静和沉稳性格在发挥着平复心灵躁动的同时,其自身因封闭而表现出的保守性与现代性话语建构之间的抵牾也日益明显。赵焰理想中的徽州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也面临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逐步扩大。
在《遥远的绘画》中,诗意人生最终没有平息小王老师一颗驿动的心。小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它既是发自刘桂兰和小王老师的心灵深处,也是作家从心底中涌出的叹息。《镜花缘》中的青年画家王明告别城市,决意用心画出徽州人的灵魂来。题为《徽州的蛐蛐》的油画,“整个基调是灰暗的,背景是徽州的老房子,飞翘的屋檐以及斑驳的墙壁,整个画面有点倾斜,很险,但又很牢固。在右下角,有一群人在斗蛐蛐。蛐蛐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几张麻木而丑陋的脸,其中有一张兴奋得完全变形……他十分兴奋地发现,自己终于寻觅到一种徽州的精神,一种现代意识与徽州古老文明撞击的火花。”徽州文化本身只有与现代意识对话才能获得新生,而现代意识离开了徽州文化或者说盲目地否定徽州的一切也会因缺乏文化的养料而枯萎,这是赵焰对徽州文化的完整而辩证的表达。但是,尽管王明的油画《徽州的蛐蛐》和《镜子里的徽州》确实准确地把握了徽州文化因封闭所呈现出的阴性特质,但王明却难觅知音。在小说中,王明的尴尬处境所表现的是徽州文化的尴尬处境,同时也是作家自身在面对古典情结与现代大众文化时的两难境地。
“古典”的现代意识
赵焰小说在描画清朗的人生图景、传达温馨的青春气息、探寻幽远的徽州故道时,虽然也间接表现出一定的现实性,但由于其小说过于追求古典的抒情性,与紧跟时代的诸多小说相比,显然不够“现代”。
实际上,小说整体上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它的现实性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躁动的现实的追逐。在欲望泛滥的时代,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坚定的民间立场的作家,赵焰敏锐地捕捉到在一个消费化、制度化的转型期社会中的精神现实的浮躁。浮躁意味着思想的苍白、人文精神的游离,并最终导致意义危机。著名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指出,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有着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分别表现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与“形上迷失”。②这种意义危机在转型期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大众文化的巨大诱惑面前,作家们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缺乏清醒的意识。问题小说的走俏便是顺应了市场热点的需求。虽然我们无法否定问题小说的当下性与现实性,但大众文化的快餐性质使得问题小说缺乏精神建构的深度和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对物质现代性所形成的人的制度化产生幻觉,从而认同人的制度化,这与现代性对于人性完善的内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艺术在一个民族现代性话语建构中的角色除了舒缓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自身独特的形式,构建连接人类心灵与时代精神的桥梁。这就需要超越特定现实具象,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构筑人文镜像,在这个镜像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人类心灵的脉搏,感受到精神的呼吸,而这些丰富的细节在现代性话语建构中的人文内涵则是赵焰所努力探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焰说对纯粹现实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实所包裹的情感、精神和一切灵性的领域才是一个作家应该努力寻找的,尽管这种努力一时还不被大众文化所认同。事实上,赵焰并不排斥艺术载道,但他认为这个道应该是一种超越具象的、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这种文化哲学因为作家自身主体的介入和文化根性的渗透而显得丰盈厚重。在赵焰的小说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家自身的心路历程和主体精神脉动中感受到时代变迁,在《春晓》、《冬日平常事》、《镜花缘》等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聆听到时代的心声;另一方面在小说《二人行》、《隔墙有耳》、《大学生小安》、《小说二题》、《黄蚂蚁》等中,我们看到作家甚至利用反讽等艺术手法直接介入现实,人性的萎缩,现实的无奈等都有所涉猎。但赵焰的艺术触角并不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具象上,现实只是他揭示意义危机的支点,以此为基础,赵焰在对徽州文化底蕴的深层把握中揭示徽州人的生命状态——古老的文化品性与现代性之间盘根交错的胶着状态。虽然赵焰无意为这种文化品行如何融入现代性话语提供具体的方案,但作家在叟、老六头、王明、“他”等人物身上倾注他理想的文化形式与人生的存在方式;对人的青春情愫的钟爱,暗示了赵焰的理想人性和文化的存在状态——青春气息所固有的刚健清新在欲望化消费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应该拥有最大限度与广度的合法性;徽州文化的超稳定性、封闭性与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之间的深层次冲突绝不能简单地以破坏文化的物质基础为代价,在深层意义上整合文化资源、转变人的生存思维才是关键。这样的文化观与生存观是以尊重和理解文化与人的生存现实为前提的,它强调宽容和理解,在与心灵、文化神韵的对话及交流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是防止人走向异化的精神支柱。至此,我们终于看到赵焰小说在古典叙事包裹下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的聚焦点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无疑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还看到,赵焰在张扬自身的现代意识时,使自己游离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欲望同心圆。我们知道,自由的心态是知识分子品格得以张扬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作家在挣脱政治工具论后,一些人又主动地放弃了难得的创作自由。一头扎进了欲望的同心圆。欲望的同心圆实际上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社会征兆。物质现代性的进展和实现必然需要制度的保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成为一种新的体制,这种体制需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氛围支持。在社会转型期,主流话语对于欲望化话语是持一种默许和鼓励态度,因为欲望是激发人们去发财致富的直接动力。知识分子当然没有理由否定这种欲望话语的合法性,但知识分子并非只能被动地适应和毫无立场地随波逐流,因为就现代性而言,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应该在于为物质现代性提供批判性质的审美现代性话语。尽管抗拒本身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略显悲壮的突破对于民族精神建构和文学自身而言却更为重要。赵焰小说没有铿锵有力的鼓舞和鞭策,但其平淡的况味与平庸的确有天壤之别。平淡中的从容可以陶冶精神和净化灵魂,有利于新时期小说的丰富和发展。
- 上一篇:团组织的吸引力弱化范文
- 下一篇:老舍战争期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范文
扩展阅读
- 1古典文化
- 2古典诗吟唱
- 3古典文学
- 4古典诗歌语言特征
- 5古典时代雅典婚配模式
- 6古典词学趣范畴承传考察
- 7古典园林建筑在古典园林中的作用
- 8古典艺术风格
- 9古典经济学
- 10古典诗吟唱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