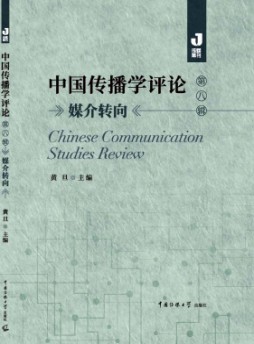从传播学视域解析手机的深层意义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从传播学视域解析手机的深层意义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继电影《手机》之后,同名电视剧再次以媒介为主题和背景,反映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描绘出当代社会媒介大发展和人际关系疏离、传统价值观念滑落之间的因果关系图谱。作为并不多见的以反映媒介问题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相较电影,电视剧《手机》将这种因果关系更为全面地铺陈开来,且把当下的诸多现实问题与媒介相勾连,并将其纳入到一幅真实的到媒介化社会的影像之中。
按理说,生活于今日“地球村”中的我们,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发达的通讯和传播工具,手机导航的精确定位,可视电话的即时交流,让我们可跨越时空界限,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困扰人类几千年的交流之虞似乎成了伪命题。但以第五媒介——“手机”命名的电视剧,却不惜笔墨揭示手机使用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处处体现出对现代社会中人际传播的焦虑。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神奇的电报初使用时,梭罗那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发问——若电报线路两端的人无话可说怎么办?[1]
手机的使用同样引发我们深思——它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心与心的距离呢,如果双方不能“有一说一”怎么办?当这个令人悲观、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传播技术条件下的人际传播问题。
一
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勒纳(D.Lerner)从传播体系的变动和整个社会体系变动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出发,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演进,划分为以口头传播系统为主的传统型社会、传媒和口头传播系统并立的过渡型社会、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系统的现代型社会三个阶段。[2]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以《手机》为例,来分析传播媒介发展对社会和人际传播的影响。
30多年前的严家庄,显然是传媒和口头传播系统并立的过渡型社会,且以口头传播为主,“通讯基本靠喊”,现代通讯技术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电视剧中许多情节可以为证:新娘吕桂花借助一部固定电话和高音喇叭向远在200里外的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之苦;移居到200里外的张小柱写给白石头(严守一小名)的信,在邮差手中即将成为“死信”时,是路之信的喊声帮助邮差完成了这次借助多种手段才完成的人际传播。电视剧在暗示,在过渡型社会中,人们仅仅在方圆200里左右的有限范围内从事着以口头交流为主要手段的传播活动。多年后,奶奶告诉严守一,小时候白石头撒过一次谎后,面对奶奶一直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原因是他耳朵后的黑痣会“告诉”别人他是否在说谎,而这个秘密只有和他非常亲近的人才会察觉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过渡型社会,虽然现代媒介逐渐侵入到偏远乡村,但并未对传统社会的人际传播模式改变多少,人际传播仍然是面对面的、非常可靠的,这进而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紧密的关系。
而当严守一成为闻名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严家庄乡亲们不仅时刻关注着他“今晚会不会上电视”,而且在他们也用上了手机后,预示着现代传播媒介将这个偏僻的山村带入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随即被深刻改变。在严家庄,“手机一响,黄金万两”,天生大嗓门的路之信借助手机传播的及时信息干起了“哭丧”营生,让这个本来穷困潦倒的光棍汉一度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婚姻生活。当年依靠固定电话和高音喇叭以及人力的中介完成夫妇间私密问候的牛三斤,这时却在一部时兴的导航手机指引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远在北京的妻女。手机在这里俨然昭示:手机就是信息,使用手机就是和现代社会的接轨,甚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乡村如此,城里人更因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而受益。自幼与传播媒介结下不解之缘的严守一当上了电视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并蜚声全国,赢得了声誉。媒介知识分子费墨,从策划电视节目、出书乃至亲自上镜走到聚光灯下而名利兼收。具体到手机,引用电视剧中的台词——“手机的应用,就一个民族来说,早十年,晚十年,事关国民经济建设;而就一个人来说,关了手机就等于关了脑子,不敢想象没手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形象地说明了手机对社会和个人的深刻影响。保罗·莱文森更是以浪漫的语言宣称,“手机把人们从机器跟前和紧闭的室内解放出来,送到大自然中去。你可以在高山海滨、森林草原、田野牧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你可以斩断把你束缚在室内和电脑前的‘脐带’去漫游世界。只需要一个用大拇指操作的手机,你就可以‘一指定乾坤’”。手机带给我们的,“一般都是净盈利”。[3]
由此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一例外地享受着手机使用及其高度介入、干预生活而带来的福祉。
若就此打住,《手机》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媒介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媒介的进步意义在此亦彰显无疑,这正是发展传播学所期望和津津乐道的。但媒介是中性的,于此是善、是进步,于彼却不见得。即使在个人身上,这种中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借助电话表达相思之苦的幸福新娘吕桂花,在30年后闹起了离婚。婚姻的变故倒不算什么,可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被铁心要离婚的吕桂花刻意否认的30年前的电话,以及上了一期电视节目《有一说一》,竟然让她无法获得精神自由,原因是“最近你还回来吗”所隐喻的爱情故事被广泛传唱,连法官都认为“社会影响太大”而不予判决。媒介作用如此之大,大得可随意左右、控制、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这还不算完,吕桂花想离婚却因一个电话离不成,从未想过要离婚的严守一却因偶然间无意拨通的电话而家庭破裂。更令人深思的是,当被严守一视为“身体的故乡,更是精神故乡”的奶奶临终时,在外的兄弟俩却都关机,错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的不可靠在这里以如此令人心痛的方式表现出来。老实巴交的牛三斤借助导航电话找到了喧嚣都市中的妻女,试图挽回濒临破碎的婚姻。尽管流浪歌手演绎的“最近你还回来吗”那饱含深情的问候,时不时地将他拉回到过往中,但感怀当年,相隔200里距离的交流看似困难重重却情意绵绵,如今传播技术将人们之间的距离无限拉近,遗憾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徒留惘然和慨叹。
毋庸置疑,手机的出现使得人类跨越了时空界限,不用面对面就可完成人际传播,哪怕相隔万水千山。如果秉承麦克卢和莱文森乐观的媒介观,毫无疑问,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且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媒介有效地补偿了旧媒介的不足,媒介在与社会的不断互动中获得自身的进化,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开创了不同的时代。[4]
但问题和麻烦也出现了,手机延伸了我们听觉感官,却为信息的缺失和个人行为的不自由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埋下了伏笔。麦克卢汉当年神谕般地、乐观浪漫地告诉全世界,“媒介即信息”,却不知这位预言家是否忧虑过这一点。
考察手机的社会功能就会发现,“一方面,手机被吹捧为进步、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前进的象征”,“另一方面,移动通信也被认为是文化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些紧张关系包括传统和现代、乡村价值和都市规范、地方情谊和外部侵犯、社区和谐与移民离散、家庭亲情和虚拟网络、个人主义和全球化如此等等之间的冲突。”[5]
不经意间,一个被麦克卢汉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无论是丹尼尔·勒纳笔下“传统—过渡—现代”的社会演进序列,还是麦克卢汉隐喻般的“部落—脱部落—重回部落”的感知方式回归,媒介技术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进步无疑改变了个人与社会,无限度缩短了人类传播的时空距离,但是,它是否也应为人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和麻烦负责?
二
传统人际传播(或称人际交流)是指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的传播行为,是一种面对面的口头传播。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口头式的人际传播逐渐扩展为媒介方式的人际传播。从固定电话的发明到手机和互联网络的广泛使用,媒介方式的人际传播已然蔚为大观,人际传播研究在传播研究当中所占的比重和分量也日益增加。彼德斯总结道,“交流”(或称传播)是20世纪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在战后,有两种话语占据了“交流”研究的主导地位:一是信息论的技术话语“通讯”,一是在人文主义框架内发展的作为疾病和治疗话语“交流”。两者都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人类接触的障碍和麻烦都可借助技术而得到改善。[6]
但事实果真这样吗?起码《手机》告诉我们并非如此。那么,新媒介介入人际传播后表征着一种怎样的传播方式?它与传统人际传播有何不同?
与麦克卢汉、勒纳不同,美国女传播学者、“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创始人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及其合作者认为,传播技术对传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否被人们以某种方式用于延伸他们通过其他传播形态业已进行的活动”,[7]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社会传播形态,也就不能以此来划分不同社会形态。依据信息流通方式,她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独白式的传播形态,人际传播是对话式的传播形态,而借助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传播,则是电子对话式的传播形态。据此分类,显然我们可将通过手机进行的人际传播归入新兴的电子对话式传播形态的范畴。洛基奇等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弄懂人类传播的基本特征,进而才能弄懂任何传播形态的潜力。为此她们列出了感觉上可靠性、地理范围、反馈性质、潜在互动性(交互性)、对于硬件及软件技术(非传统的语言技巧)的依赖等10方面的特征或称评判标准,以此为尺度去对比分析传统人际传播形态同以信息传播新技术为手段的新兴传播形态。在电视剧中,奶奶质疑通过“没有线的电话”——手机——能和远在北京的严守一“说上话”,她朴素的理由,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因在场感的缺失而导致交流不可靠。而传统人际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传播,除有声语言外,姿态、外观形象等都是自我表达的手段与媒介。[8]
虽然“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具有接触的感染力。”[9]
但当手机、QQ、MSN等通讯工具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主体间交流中时,人际传播“多媒体”的优势和功能大幅缩水,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交往失真。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延伸了人的感官,对传播个体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对个体间的交流来说,电子媒介的介入却使人们的感官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际传播在感觉上的可靠性和反馈的完整性。通过电话(手机)进行的中介式交流与互动使得人际交往越来越“缺乏任何共同在场形式”,这种“无声化”、“间接性”和“非共同在场性”的特征与人们在面对面情景中的人际互动模式差异极大。[10]
“因为所有中介物都只是某种工具性媒介,他们无法像面对面交往那样,通过对方的表情、语调、姿势、服装、配饰等非语言符号来辨别交往双方内心真实的情绪体验与情感状态。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强了。”[11]
显然,连一向对传播媒介保持乐观态度的莱文森也看到了手机对于人际传播的负面影响,他不得不承认,“除了给人带来好处之外,手机可能开启了一个说谎的黄金时代”,“手机号码叫做你的监号(cellnumber)”。[12]
手机让人身不由己,怕被猜测而撒谎,因撒谎而疏离,人际关系不再是面对面交流而心连心,变成了面对面(通过手机短信)的撒谎和心与心的隔阂。在电视剧里,严守一、费墨等人算不上道德的堕落者,但手机在手,让他们谎话连篇——“手机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拿起手机你就言不由衷”。手机这个中介不断地引诱着他们说出谎言,在潜移默化中异化着人,引导他们走向撒谎和欺骗,进而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13]
至此,似乎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媒介的广泛运用,以手机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介入,使得原本纯粹、高效、可靠的人际传播变得面目全非,人际关系也随之不断疏离、扭曲甚至恶化。在结尾处,电视剧也以这样方式表达对媒介“恶”的逃避、控诉与反思——伍月扔掉手机离开了都市,严守一奔向“宁静、有海”的爱沙尼亚,两年中音信全无,费墨则告别了喧嚣的电视媒体回归大学校园。
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寄望于技术来增进交流无异于痴人说梦。“交流的缺陷仰仗于技术,可是任何技术都不能十全十美,新的技术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就苛求更新的技术。在彼得斯看来,人类的交流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循环的技术矛盾体:技术既是病人又充当医生。”[14]
另一方面,将现代社会中人际交流的失败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一社会现实,完全归罪于手机的介入,或视为媒介进步开出的“恶之花”,也是不妥当的,彼得斯同样告诫人们,“抱怨媒介扭曲对话,就像是哭丧找错了坟头”。[15]
综合以上两方面,质言之,媒介既无法促使交流趋于完美,也无力扭曲对话。
那么,人际传播实质到底是什么?人们如何才能达到真实交流的目的?《手机》对媒介的批判难道做了无用功?
传播学的先驱们将传播归结为直线的信息流通模式,人际传播始终也在“我说你听”以及“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的圈子里追求最佳效果。因此,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传播,还是印刷和电子媒介介入其中的人际传播,处处体现的是讯息、控制、效果的拉斯韦尔5W模式。洛基奇笔下的“电子对话式传播”就是以“传播是信息流通”为宗旨,将其和传统的人际传播相比较,得出了传播不在场、“感觉上的可靠性”下降,传播的质量因此被削弱等结论。当人们在为新传播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欢呼,以及对交流的负面影响进行批判的同时,却也给传播笼罩上“技术的”光环。
近几十年来,“传播就是共享”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认。传播取“共享”的含义,旨在强调传播的相互性,是指参与其间的人们共同在做的事情。而人际传播,则是“一个相互的、持续不断的、协商的、合作建构意义的交流过程”。[16]
在传播中,即建构、共享意义的交流过程中,人不仅造就了自身,也在双方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各自对对方行为产生了期望,人际关系得以形成。因此,人是关系的存在,构成人类世界的本质是关系。关系就成了研究人的问题的起点,也是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传播学研究试图从个体相遇和交流的角度,界定人际关系的发生和发展。”[17]
在这种视角下,人际传播的不同形式以及因之带来的问题“都不是决定和导致高质量传播的最重要的因素”,人际传播强调人与人个性的相遇交流,“只有相互尊重个体间的自我属性,人与人才得以保持这种特殊的关系,并使之渐入‘我—你’传播的佳境。”也就是说,判断人际传播是否达到理想的效果的重要标准只有一个,即个体间“自我属性”的相遇。[18]
这里说的相遇便是,人通过传播与交流,由彼此相处,而相互了解的交往过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参与其中的个体是充满个性特征的人,影响人际传播质量的,不是别的,而是是否向对方传播一个真实的自我。
这种自我属性的相遇关系和敞开心怀的体验交流,在犹太哲学家、思想家马丁·布伯那里被称之为“我—你”的对话。“我—你”关系理论是人际传播思想的精华。在其最重要的著述《我与你》中,布伯认为人身处双重世界,一重是“我—它”,另一重是“我—你”。[19]
“我—它”关系的世界,是由与我们相对立的客体,包括我们可以利用的人与物的关系构成。“我—你”关系的世界,是一种相互融合的世界,人的自我不断通过互动得到确定。“你”、“我”在相互分享这种关系后,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之人。这种关系的形成,则需要人们进行“对话”,“对话是人与人的相遇”,而非观点、意见的相遇,对话中的人要承认他人的平等存在,把他人视作一个已经和你发生关系的人,而不是一个物品,一件东西。
如此说来,人际关系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通过自我揭示、信息反馈以及对他人自我揭示的敏感程度来进行的。弄虚作假、言行不一、反馈乏力以及自我坦露时保守拘谨都会加深关系中的误解与不满。理想的人际关系要求人们允许别人充分地体验他们,也能敞开心扉充分地体验他人。[20]
诚然,有无媒介参与,对人际交流的效果和人际关系的确立并非充分和必要条件。《手机》结尾以主人公都放弃手机的方式表达对“技术的对话”的批判,但这并不代表编剧对手机、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的最终观点,电视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细节值得玩味,也进一步申明了人际传播的实质:婚礼上,身为台词老师的沈雪和丈夫分别用有声语言和手语默契地表达出“和你用心灵交流,因为心灵的语言,才是最真实的语言”。通过手语老师和台词老师的结合,电视剧就以隐喻的方式发出对真实交流的呼唤和寄语,告诉人们要做到心与心的相连,只有通过“自我属性”的相遇也就是心灵的交流。这无关乎有声语言,更无关乎媒介是否在场以及先进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