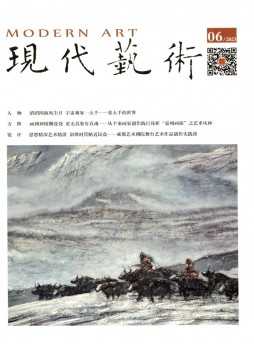华忱之的现代文学研究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华忱之的现代文学研究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近年来,王富仁、钱理群等学者在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经验和学术传统时,都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精准的学术眼光,描绘出了一副“多点共生”、“众声喧哗”的上世纪80年代研究地图:“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除了北京的李何林、王瑶、唐弢,上海的贾植芳、钱谷融外,还有南京的陈瘦竹,山东的田仲济、孙昌熙,河南的任访秋,陕西的单演义和四川的华忱之等。1作为建国后四川大学现代文学学科重要奠基人的华忱之先生,2014年是其诞辰100周年,可我们发现学界不仅关于先生的纪念文章寥寥,甚至连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多不知晓。情势如此,原因自然不一,但学术研究重“中心”轻“边缘”的地缘性特征亦难脱其咎。而我们对华先生的深切纪念,对学科偏陋的实际纠正,都离不开对其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进行认真研究和总结。
华忱之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四川大学的相遇,有待于新文学史课程的设置和高等院校调整两个要素的形成。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并成立课程改革小组。2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将“中国新文学史”设置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必修课程,学科创建之初,专任教师奇缺,许多学者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华忱之与王瑶、单演义等人在不同的地域“顺”势而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开始,华忱之与蒙文通、蒙思明、缪越等学者一道,由华西大学调任四川大学。3此后,他与林如稷、李昌陡、陈思苓、易名善等成为现代文学教研室的第一批成员。综观华忱之的现代文学研究,其对象主要集中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曹禺等几位经典作家上。如果不为尊者讳,我们很容易发现华忱之的话语体系中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比如将鲁迅和曹禺等作家的创作道路,描述成逐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历程。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寻找出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这是懒惰主义;若以此来否定一位学者的学术造诣,这是虚无主义。实际上,上述类似的话语,很难看作是华忱之独有的思想结晶,而更宜视作整个学术界不可违抗的权威性解释。我们如何排除这些广泛存在的官方定义和宏大命题导致的表面干扰,发现学者本人对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性观照和对文学现象的独特评断?首先,他在80年代初即呼吁加强对现代文学研究中薄弱环节——抗战文艺的研究。华忱之的忧虑不仅是对80年代以前抗战文艺研究情况的历史总结,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研究成果偏少的背后,还隐含着“价值估计不足”、“正面战场关注不够”等一些深层问题。
他本人在新时期对经典作家抗战期间创作的研究便是对其呼吁的最佳实践。比如他发现一些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杂文散文语焉不详甚至只字不提,于是作了《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杂文》,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杂文集《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羽书集》所收,大多偏重于动员大众的抗战宣传”,“《蒲剑集》、《今昔集》中收入的则多是关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有关屈原研究的一些文章”,并呈现了郭沫若的斗争精神、人民本位意识和“文化界领袖”的作用。5除此,华忱之还搜集整理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旧体诗文佚作,并对郭沫若的《归国杂吟》《战声集》《蜩螗集》《潮汐集•汐集》等旧体诗进行了知人论世的阐释,凸显了郭沫若“爱国抗日的思想感情,以及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华忱之对于曹禺、田汉在抗战期间的文艺研究更侧重在史料的发掘和阐释上。他以话剧《黑字二十八》和曹禺所作的戏剧讲座《编剧术》为中心,记录了曹禺在抗战初期的一些创作活动。对于曹禺解放前关于戏剧理论和编剧方法唯一的且“印本不多,流传不广”的一篇讲话,他详细介绍了其版本出处,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撮要简述。此外他还介绍了1938年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一届戏剧节纪念大会上的《全民总动员》的演出概况,并将曹禺和宋之的合作完成的四幕话剧《黑字二十八》与《全民总动员》的异同进行了重要的辨析。7华忱之对田汉在抗战期间活动及贡献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田汉与《抗战日报》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田汉1938年在长沙创办《抗战日报》的艰辛劳作,并对“保存不多”、“残缺不全”的《抗战日报》的《创刊之词》、重要作品如田汉的抗战京剧《新雁门关》等做了重要的史料重述。8其二,他特别强调“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的治学方法。作为这个学科第一代学者,华忱之“一贯强调立说著书,必须在继承借鉴,批判吸取中外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别辟蹊径,独创新机”
在“融贯中西古今”的理念自觉下,华忱之能迅速洞悉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中的中国民族特色和外国文化影响,并以能否批判性地吸收古今中外文艺经验,作为评价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准。当然,华忱之对“中西古今”的强调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遵行“延安讲话精神”,创作“具有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的群众的新文化”的五六十年代,他不得不跟随“厚今薄古”的时代主调,但依然曲折而执着地表达着他对古典传统的敬意。在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所作的《继承民族传统,发展诗歌创作》上,他强调:“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是主要的意面;但批判地继承中国民族、民间的优秀文艺传统、吸收外国进步的文艺遗产……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并指出现代诗歌要向古典诗歌学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形式运用和讲求韵律”、“刻画艺术形象和熔铸语言”等方面的优点。10到了八九十年代,在一个更加自由的学术空间中,华忱之的鲁、郭、茅、曹研究不再局限于强调这些经典作家所受的经典传统影响,而是直陈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比如《鲁迅对中外文化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一文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角度详述了鲁迅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借鉴。在《继承传统,借鉴外国》一文中,他更将茅盾和郭沫若进行了横向比较,将二人卓越的文学成就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西方文艺的借鉴”基础上。
尽管华忱之一再强调所有的继承和借鉴,都必须建立在“有分析有批判”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上,这显然有失牵强。可如果联系到80年代初整个现代文学学科普遍认为“离开了对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联系的考察,就不可能弄清现代文学的‘现代化’特点”,那么这种“牵强”的强调则实属其来有自。它既是学者个人顺应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心理趋势的自然反映,同时也是他们这一代学人压抑已久的文化多元化和文学现代化思想的集中绽放。其三,他强调文学研究必须关注作品本身的分析解读。这种似乎并无新意的呼吁其实具有极强的历史和现实针对性,即反对“单纯用思想性分析代替艺术性分析”、“把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性分析互相割裂开来,孤立开来”,而应该“把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因此,他在五六十年代的课堂上,就非常注意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他的学生曾就此批判他“用了很多时间对闻一多臧克家前期的诗作,从题材的选择到字句的推敲,作了仔细的讲解。相反,对张志民的‘死不着’,及柯仲平的一些诗,则寥寥数语,敷衍了事”。中文系召开的检查批判大会,也将其教学中“偏重作品的艺术技巧,忽视作品的政治内容”作为他“错误”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对曹禺剧作的研究上,华忱之可谓最全面深入地贯彻了他的作品的细腻分析和对作家的深切理解。比如评论界曾长期认为《雷雨》“是以蘩漪和周朴园的矛盾冲突为中心的”,他则认为“侍萍与周朴园的矛盾才应该是《雷雨》戏剧冲突的中心和主线”。16此外,有论者常将蘩漪看作“向周朴园进攻的主将”,而他并不认为蘩漪与周萍的“畸形的病态的‘乱伦’之爱”是个人解放的正当之路,对蘩漪的反抗性也持保留态度,认为“她毕竟是一个‘旧式女人’,因此,她既不可能像《伤逝》中子君那样,也不允许像娜拉那样,毅然决然冲出封建牢笼,另寻新的出路”17。比如他对《日出》中陈白露“竹均时代”和“白露时代”的矛盾纠葛;对《北京人》中思懿的“虚伪,自私,诡诈,泼辣,口蜜腹剑的戏剧性格”,曾文清的“软弱,萎靡,空虚而懒散”,愫芳“从梦幻到觉醒,从觉醒到出走的曲折过程”概括得都颇为精当。特别是他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认为是失败之作的《原野》别具慧眼,高度肯定了“《原野》在曹禺的创作道路和美学追求上,别辟蹊径,独具一格,表现为曲折的前进,而不是‘前进中的曲折’”20。因为强调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同情,所以华忱之特别反对文学研究的先入之见。这一面体现在批评左翼作品政治诉求影响了艺术性探索,指出抗战初期的作品“由于政治任务迫切,作家们廉价的热情的发洩,因而往往写的不深刻”;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武断保持警惕,比如深刻地指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批评刘绍铭抱着曹禺“作品华而不实”的“艺术偏见”做研究,难免贬抑失当。23这种两面开弓,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眼光即使在今天也是难得的。二如果要为华忱之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研究转向的学术道路和对融贯古今中西的强调、对作家作品充满理解之同情的学术特色寻找背后的“故事”,那么“清华学风”是其极为重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动力。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北京高校学科体系中,古典文学在大学文学院尤其是文学系的课程体系中仍居正统。清华中文系从1928年起制订了详细的课程表,中国文学史、文选、诗、赋、词、戏曲、小说等各体文学课程成为必修课,此外还开出过《乐府》《歌谣》《诗经》《楚辞》《唐诗》等选修课。1933年课程调整后,诸如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国学要籍、中国文学史等国学课程仍是最基础的必修课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主讲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杨树达、陈寅恪、赵元任、俞平伯、王力等知名学者。华忱之肄业清华期间,深受陈寅恪、闻一多、刘文典、钱穆等先生影响,对考证、校勘、考据和唐诗、清代朴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过着“在学问里找到了非常的愉快”的“学生派的生活”。25此后,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孟郊年谱》还因取材广泛,引用文献书目达一百二三十种,考证方法不拘一格,深受闻一多先生称许,认为:“本系历届毕业论文,用力之勤,当以此为首屈一指。”26另一方面,杨振声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1928—1930),曾提出“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的教学方针。
中文系进入了所谓的“新文学试验时期”,开始为学生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朱自清主讲)、当代比较小说、高级作文等课程。加之,清华大学戏剧教育和戏剧活动相当活跃,华忱之耳濡目染,自然对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更何况华忱之钦慕的闻一多、朱自清在将研究的重点和兴趣转向古典文学前,就已经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了。所以,如果说朱自清、闻一多一代是在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发现了古典文学的价值,那么华忱之、王瑶这一代更像是从古典文学的趣味中,感念到现代文学的情怀。清华中文系对外国语言和文学的重视也是一贯的。中文系早期规定必修的外文课程达24学分,1933年后改为18—22学分,约占本系必修课程总学分的1/5左右。其中外语方面除必修两年英文外,还鼓励选修第二外语。外国文学方面,早期要求必修西洋文学概要和西洋文学专集研究。此外还鼓励学生选修现代西洋文学、中西诗之比较等英文讲授的课程。29华忱之强调借鉴外国文化对于作家创作和学者研究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渊源即在此。实际上,他的清华同学王瑶也特别注重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前后著文《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这再次证实了“清华学风”对一代学者的深沉镌刻。华忱之强调深入时代和生活、深入人物形象,对作家作品报以理解之同情,也与“清华学风”息息相关。1988年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借用了冯友兰关于近代学术史“信古”、“疑古”、“释古”的论断,来概括清华文科的学风——“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文虽以闻一多、朱自清的研究为此论表率,但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主张,可视作对“释古”的回应和发挥,且可视作对“清华学风”的另一种表述:“主张对历史书写者或阐释者的‘主观’性进行正面的规训:即通过对古人立说之环境、背景以及对话对象的‘真了解’,而在‘神游冥想’中与古人出于‘同一境界’,从而作出合理的批评与阐释。”
王富仁曾区分过两种学者,一种是“实中求是”之人,因为这个“是”是自己“求”出来的,不同于当时世俗的见解,所以“孤傲”——文求“是”,行为“理”,人尚“独”。还有一种是“是中求实”之人,因为“是”的是别人及其作品,所以不“孤傲”,没有架子——文求“实”,行为“事”,人尚“真”。前者如陈独秀,后者如单演义。32其实,后一类也包括华忱之这样的学者。但华忱之这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又岂是一个“真”字所能概括?他们曾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随后又是这个学科的守护者,之后还是这个学科的传递者。他们捍卫经典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正面意义,同时也为作家们被忽略被贬低的特色和价值辩护;他们强调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同情,这也构成了80年代的主体性思想萌生的本土性资源;他们还引导着现代文学学科和年轻一代学人始终与优良的学风学统紧紧相连。他们身上的确难以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某些束缚,也可能缺乏丰富的研究著述,但是他们的许多研究和判断至今仍然鞭辟入里,他们曾经的许多忧虑和期待至今仍然亟待解决。
作者:康斌 单位: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