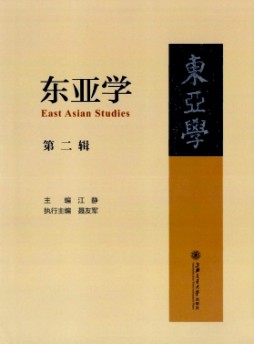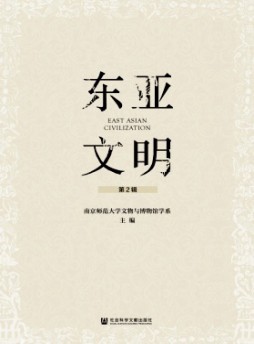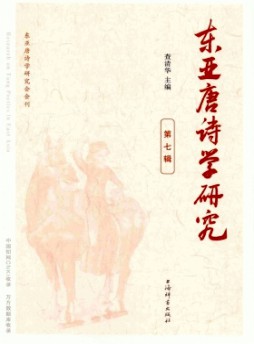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研究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研究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西部学刊杂志》2014年第八期
②各国在救灾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形成了“一轴心两大国三层次”模式,即由“一组织轴心机制;两大国推动机制;三层次协同机制”构成的救灾合作机制。而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的建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与东亚合作机制相吻合,且对现有的合作机制产生依赖。
1.从“一组织轴心机制”看路径依赖的“惯性”路径依赖就像物理中所说的“惯性(inertia)”,一旦采取某种路径(无论好与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这里着重分析一下“一组织轴心机制”的“惯性”。“一组织”指东盟(ASEAN),“东亚地区合作以1967年东盟的成立为标志,开创了地区合作‘小车拉动大车’的新模式,形成了以东盟为圆心,向外依次是‘10+1’、‘10+3’和东亚峰会等多轨并存的合作机制”。[6]1以东盟为轴心的东亚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10+3等机制,而救灾合作均依赖于现有的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每年召开一次救灾会间会,制订了《ARF地区论坛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战略指导文件》、《ARF减灾工作计划》、《ARF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声明》和《ARF救灾合作指导原则》等框架性文件。这一救灾合作机制依赖于以东盟为轴心的东盟地区论坛这一机制。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防灾减灾成为10+3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及《2007年-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提出了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措施。2007年-2008年,中国举办了两届10+3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探讨了加强武装部队国际救灾协调机制建设、标准操作程序和法律保障等问题。2010年,“10+3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减灾是2007年1月第二届东亚峰会确定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9年第四届东亚峰会发表《东亚峰会灾害管理帕塔亚声明》等。当“救灾”成为东亚合作的新领域时,救灾合作并没有出现“路径创造”,开辟新的路径进行救灾合作,而是在东亚原有的合作机制下采取“路径依赖”,按照路径依赖的“惯性”进行合作。当然“两大国推动机制与三层次参与机制”涉及救灾领域的合作机制的建构也是基于路径依赖的“惯性”。2009年10月25日通过的《东亚峰会灾害管理帕塔亚声明》指出“:支持东盟努力加强人道主义协调并增强应对重大灾害的领导作用。”而这与国际社会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表态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盟10国的作用还不仅只表现在目前的领导作用上,更体现在它为促成东南亚地区一体化以及积极倡导和推动东亚合作两个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方面。”“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了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核心’作用,并声明对之予以支持。”东亚救灾合作领导权来源于东亚合作领导权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2.从“两大国推动机制”看“历史的作用”“路径依赖概念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组织的结构和制度的结构是从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事情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使之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这条路径是在对过去事件的适应下产生的。”[8]在东亚救灾合作机制建构中,笔者以“两大国推动机制”为例谈谈路径依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两大国”指中国和日本。目前,中日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经济规模可以与欧盟和美国相媲美,且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容小觑。“历史上,中国曾在东亚建立了‘朝贡体系’(tributarysystem),日本打着‘把亚洲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开始向亚洲进军,东南亚经历了1942~1945年的日本直接统治时期。”[6]45基于中国自晚清后的一百余年陷入衰落,日本对东亚的殖民入侵及二战战败,美国入主东亚等原因,战后中日两国都无法独自领导东亚,东亚合作的领导权不能旁落外戚美国之手,东亚合作的领导权落在自1967年不断成长,但实力仍较弱的东盟身上。东亚合作机制的建构就是经典的制度路径依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虽日本战后因美国的扶持国力迅速恢复,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也步入快速复兴轨道,中日两国实力在东亚目前均属“超级大国”,但在东亚合作中却只能扮演“推手”的角色,这就是“过去的事情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中日两国在东亚救灾合作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如同其在东亚合作机制建构中的作用一样,在救灾领域东亚依旧玩着“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游戏,而中国和日本只能扮演着“助手角色”。如日本倡议的“亚洲减灾中心”成立于1998年,中日都是核心成员国。中心旨在提升成员国应对灾害的能力、建设安全的社区、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主要开展四方面的工作:减灾信息共享、人力资源培训、社区能力建设以及相关国际会议和交流。中国首倡的“亚洲减灾大会”是亚洲各国和利益攸关方开展机制化减灾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平台。2005年在北京召开首届大会是第一次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此后,亚洲减灾大会召开过3次,形成了《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减少灾害风险德里宣言》、《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吉隆坡宣言》、《仁川宣言》和《亚太地区通过适应气候变化减轻灾害风险仁川区域路线图》等成果文件。由此可见,中日推动东亚合作的野心不局限于东亚地区,从“亚洲减灾中心”与“亚洲减灾大会”可见中国和日本倡导的救灾合作机制首先不是局限在东亚地区,而是亚洲层面。东盟10国基于对中日“历史”的认知,警惕之心常在,东亚事务的主导权不肯轻易旁落中日。这里制度路径依赖的“历史”既指东亚地区过去发展所经历的一切,也指东亚合作所已建构并可用于救灾合作的现有合作机制;这里的“现实”既指东亚合作制度安排的现实,也指东亚灾害频发,救灾合作成为东亚共同关切这一基本判断。总之,中日在东亚过去的作为、当下的国力及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他们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一地位和作用与当下东亚救灾合作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在救灾领域的角色。
3.从“三层次协同机制”看制度的“自我强化”“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尘埃实际上永远不会真正落定’,即制度永远处于不断地演化之中。”[8]东亚救灾合作机制建构首先在“超区域层次”启迪下逐步展开,联合国在1987年12月的第42届大会上,把20世纪90年代定为“国际防灾10年(中国一般称为‘国际减灾十年’)”,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UNDRO)1991年2月11日至15日在曼谷召开了国际减灾十年亚太地区会议。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2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会议。[10]“1995年ARF通过了《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提出了东盟地区论坛发展的近期和中长期具措施。无论是在中长期计划还是在近期开展的‘第二轨道’活动中所包含的主要内容都包括了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减灾援助的动员合作机制。历次ARF救灾会间会都将救灾合作作为重点议题来讨论。”[11]1994年5月,作为中期回顾和指向将来的“国际防灾10年世界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日本由此展开“亚洲防灾会议”的推进工作,1996年10月在东京举行“亚洲防灾专家会议”,1997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亚洲防灾合作推进会议”,日本倡议的“亚洲减灾中心”于1998年7月30日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成立,随后定期召开“亚洲防灾会议”于2002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2003年1月在日本神户等地每年召开。[9]56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防灾减灾成为10+3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及《2007年-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提出了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措施。中国首倡的“亚洲减灾大会”是亚洲各国和利益攸关方开展机制化减灾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平台。2005年在北京召开首届大会是第一次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减灾是2007年1月第二届东亚峰会确定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9年第四届东亚峰会发表《东亚峰会灾害管理帕塔亚声明》,包括支持灾害管理能力建设合作;开发本地区一体化、跨界及多灾种的备灾能力、彼此相连的早期预警系统和应对能力等。2009年10月31日,首次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部长级会议在日本举行,会议通过了《灾害管理合作三方联合声明》,自此由三国轮流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中日韩三国就救灾合作展开了积极对话。从东亚地区救灾合作机制的建构历程可以看出,东亚救灾合作机制演化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机制建构越来越具体化,从层次上来看,表现为从超区域层次向区域层次,从区域层次向次区域发展的态势。首先是联合国“国际防灾10年世界会议”落户亚洲,促进了亚洲层次的“亚洲防灾专家会议”、“亚洲防灾合作推进会议”、“亚洲防灾会议”等救灾机制诞生,然后是区域层次“东盟地区论坛救灾会间会”“、东亚峰会”等,到次区域层次“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部长级会议”等。二是机制建构越来越深化,如1995年ARF通过了《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提出了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减灾援助的动员合作机制,到ARF救灾会间会的召开,《ARF人道主义救灾和减灾战略指针》和《ARF减灾工作计划》的制定、2009年和2010年第一届和第二届ARF武装部队国际救灾行动法律规程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到2008年“东盟地区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和2011年ARF救灾演练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拉威西省万鸦老市举行,ARF框架下的救灾合作机制在ARF制度路径依赖下通过不断“自我强化”得以优化。当然,救灾合作机制中如救灾演习、ARF武装部队国际救灾行动法律规程建设等内容是原东亚合作机制中所没有的,属于依赖于ARF的“路径创造”。“Arthur和David曾指出报酬递增是路径依赖形成的必要条件。”[5]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的建构是在东亚合作机制的路径上拓展合作内容,使原合作机制发挥了更大的效益,这就是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
二、制度路径依赖对东亚救灾合作的影响
1.积极影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概念来源于人们对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feedbackmechanism)的开放系统的认识,所谓正反馈机制就是一种系统的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是指,受到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某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12]一是东亚可快速建构起救灾合作机制。东亚合作机制总领先于了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的建构,东亚救灾合作沿着东亚合作的路径(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10+3等)展开,所以东亚地区很快建构了“一轴心两大国三层次”模式,即“一组织轴心机制;两大国推动机制;三层次协同机制”的救灾合作机制。“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13]东亚救灾合作机制也将在日后救灾合作中得到发展和演进。二是有利于形成东亚救灾合作的机制保障,促进东亚救灾合作的开展。“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维持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14]东亚救灾合作在现有的救灾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救灾会间会、东亚峰会、10+3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文件等是东亚展开救灾合作的机制保障,因为这些机制建立在东亚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不会因为某年份某段时间没有灾害发生而忽略这一合作,当然本地区灾害的发生,特别是巨灾的发生无疑将促进这一合作的开展。三是有利于提高东亚救灾机制的稳定性,实现救灾合作可预期。“路径依赖强调系统变迁中的时间因素和历史的‘滞后’作用。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系统便陷入锁定状态,即出现报酬递增、正反馈、自增强现象。历史的‘滞后’作用既可能是历史事件的结果造成的,也可能是历史本身内在的性质(内在的规则和秩序)造成的。但一旦临界值达到一定的水平,在累积和自增强过程的作用下,系统就会被锁定在某些状态而很难脱离现有的发展轨迹,进入更有效的可替代轨迹。”[1]制度路径依赖的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同样,基于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东亚救灾合作机制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增强了,这种合作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将有利于本地区救灾合作的开展。
2.消极影响“路径依赖是资源配置过程的一个动态特征,它讨论的是动态过程及其演化结果之间的关系,或是一个随机过程的概率分布情况。”[15]“North比较研究了英国与西班牙、北美与南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认为是偶然因素、制度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等自我强化机制决定了制度选择和路径变迁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大量低绩效或无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1]一是东亚救灾合作陷入东亚合作一样的困境:以东盟为主导还是以东盟为主体。“主导权是指地区合作中具有决定性指导地位,一般是由某个国家或集团承担,其发挥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要比其他国家要多要大要强。”[16]8东亚救灾合作依赖于东亚合作路径,东盟发挥着“驾驶员”的角色,开创了地区合作“小车拉动大车”的新模式。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东盟作为地区主义的倡导者,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切实可行的。”[17]11但由于东盟的“权力平衡外交”(balanceofpowerdiplomacy),不断拉拢域外大国来平衡域内大国,采取典型的“东盟规范”③处理外交关系,使东亚合作进程缓慢,东亚一体化程度不高,形成了对东盟10个小国更加有利的局面,东亚域内中日等大国对东亚合作发挥着“与本国实力与抱负不对等的作用”,而救灾合作的推动,除现有的机制外,还靠一国的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加以保障。所以,在救灾合作中,东亚依然面临着调整中-日-东盟三驾马车之间关系问题,要让中日做东亚的“主人”,而不是东盟的“客人”。只有这三驾马车形成合力,东亚合作,包括救灾合作才会快速稳步推进。二是东亚救灾机制形式多、内容不实、效率不高。东亚救灾合作机制依赖于东亚合作机制,从超区域层次到次区域层次,救灾机制较多,从联合国“国际防灾10年世界会议”、“亚洲防灾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救灾会间会”到“10+1”、“10+3”、“10+6”、“10+8”和“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部长级会议”,从创建“亚洲减灾中心”到“东盟地区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总之,各种机制下都“找机会谈谈救灾”,缺乏对救灾合作机制建构的整体规划,也缺乏像构建灾害预防体系、救灾物流体系、灾后恢复重建合作机制等实质性的合作机制。这是东亚救灾合作严重依赖东亚合作的不良后果,东亚合作本来面临的挑战较多、议题较为宽广、国家间差异大,救灾合作的议题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将对东亚救灾合作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早期细微的差别很容易导致后期发展路径和绩效的巨大差异。”[1]东亚救灾合作在哪个路径下推进、在哪个范围内推进更好,因一开始路径选择的差异,也很难“殊途同归”。三是因路径依赖,创建科学的东亚救灾合作机制面临挑战。许多学者认为东亚救灾合作的机制不够健全,但“学习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人们学会了在给定的制度下更快地工作,这种‘干中学’带来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8]“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正如诺斯所说,方向的扭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13]所以,要建立比较完善的东亚救灾合作机制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结语
总之,东亚地区依赖东亚合作机制路径,形成了“一组织轴心机制;两大国推动机制;三层次协同机制”的救灾合作机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是North根据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路径依赖理论提出的,他认为“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路径变迁路线的力量之一。“路线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4]134已有的东亚合作机制及东亚灾害频发与当下东亚救灾合作机制路径选择紧密相连,也将影响未来东亚救灾合作的深入开展。
作者:何章银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