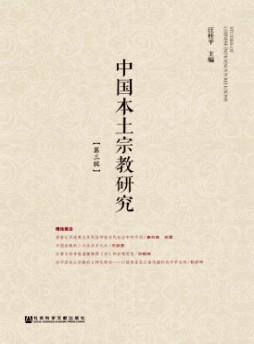本土研发和国际技术的演化及效应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本土研发和国际技术的演化及效应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科学学研究杂志》2015年第八期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难以独善其身,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资源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技术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如何利用全球资源提升国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已经成为后发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技术贸易不仅是国际资本和商品流动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进行知识转移和溢出的重要载体。Coe和Helpman[4]较早提出运用国际贸易作为知识流动的载体。Eaton和Kortum[5]研究发现OECD国家增长中50%的创新驱动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但是Zhu和Jeon[6]的研究表明双边FDI的正向效应相对较小。陈菲琼和丁宁[7]认为企业通过OFDI嵌入全球化网络,可以有效地接近产业专门性资源以及共享制度和公共资源。王华,赖明勇和柒江艺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许可对中国企业自生能力的培养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跨国公司是FDI、国际贸易和研发国际化等活动的组织载体。Patel和Vega、Gerybadze和Reger[10]等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复杂化的跨国公司研发组织全球分布模式,徐康宁等进一步考察了跨国公司研发组织全球分布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问题,陈劲等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正在转变,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模式;冯德连[15]则认为中国应采取自主创新为主,模仿与合作创新为辅的组合模式。作为后发国家,科技全球化对中国科技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薛澜和沈群红[16]指出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重构国家创新体系,江小涓[17]则提出利用全球化机遇提升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
现有研究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技术升级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国际技术转移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韩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佐证;另一方面,很多新兴国家通过国际技术引进不但没有使产业技术能力升级,反而受制于国外技术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魏守华,姜宁和吴贵生[18],Fu和Gong[19]对中国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引进的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实际上,在全球分工的知识经济时代,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两者都不可或缺,关键是如何使两者组合效应最大化。为此,本文拟在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揭示G7国家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演化路径,分析两者组合模式的效应,为中国组合模式选择和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方法和数据
1.1分析框架根据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框架[20],一国创新能力的成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研发强度,而且还得益于国际技术流动。传统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仅仅考虑了本国研发强度,没有将国家知识生产活动纳入全球化背景中,考虑国际技术流动的效应。实际上,国际技术(知识)流动也是影响产业技术升级和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要素,人才、经费和设备等创新要素跨国流动的本质是它们隐含的显性或者隐性知识的跨国扩散。从投入产出的视角而言,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通过研发投入获得创新产出的系统。研发投入强度是国际技术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只有达到一定的研发强度才有可能消化和吸收国外流入的技术,进而将新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国际技术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创新体系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资源、改善创新效率和提升创新能力;国际技术流出是技术流入和本土研发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新技术扩散和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逆向学习的过程。为此,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基点。
1.2样本选择本研究选择七国集团(G7)作为研究样本,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①。样本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考虑:第一,尽管近年来金砖国家(BRICS)(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序不断攀升,但是G7国家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出版的世界经济瞭望数据库(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②,2013年世界经济排序前6位的经济体中除了中国(第2位)之外,其他5位均为G7国家成员,排序第7-11位的分别是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印度和加拿大。显然,G7+BRIC组成了世界经济Top11的国家,G7国家是经济总量规模最接近中国的样本;第二,长期以来,G7国家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是全球研发经费支出的主要贡献者,1991年G7国家研发支出占全世界研发支出的96%,尽管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增长迅速,但是2012年G7国家研发支出仍然占世界研发支出的64.66%③;第三,在全世界技术贸易总额中,发达工业化国家在技术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约为80%,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五大工业强国占发达工业化国家技术贸易总额的90%④。虽然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广泛参与国际技术贸易,但是G7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仍然主导全球技术流动。第四,G7国家包括了全球主要的创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尝试在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可以为历史演化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资料,为中国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经验借鉴。
1.3指标选取借鉴现有研究[20],本文采用研发强度(RD)-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ERD/GDP)作为本土研发努力衡量指标。采用技术国际收支(technologybalanceofpayments)⑤作为国际技术流动的衡量指标[21]。技术国际收支具体包括技术国际支出(payments)和技术国际收入(receipts)两个指标。考虑到国际技术流动具有方向性,为了充分考虑技术流入和流出之间的平衡,本研究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简称RCA指数)测算国际技术比较优势指数(IA)。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2]于1965年提出了RCA,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本文采用与RCA指数类似的原理,构建国际技术比较优势指数。所谓国际技术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国技术国际收入额占其技术国际支出额的份额与全世界技术收入额占全世界技术支出额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1.4数据来源R&D经费数据来自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G7国家国际技术比较优势指数根据国际技术平衡数据进行计算(结果见表1),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Bank)统计数据库。从表1中不难看出,1985和1986年英国和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从1987年到1991年只有美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他G7国家主要是比较劣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兴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技术贸易,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相继呈现出国际技术比较优势,而美国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下降。
2本土研发努力与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演化
2.1本土研发努力-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矩阵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分析二维矩阵[20]基础上,通过两个方面的改进提出本土技术研发强度-国际技术比较优势组合模式矩阵。第一,将国际技术流入和流出整合成国际技术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直接考察技术研发强度与技术比较优势之间的组合关系;第二,将指标强度高/低划分标准从不同时期平均值调整为固定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矩阵的适用性和提升研究结果的政策内涵。普遍认为,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是进入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基本条件[23],为此,将本土技术研发强度高/低的标准设定为2%;国际技术比较优势的高/低的标准设定为1,当技术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表示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外部技术供给驱动向外部技术需求拉动转变。根据本土技术研发强度-国际技术比较优势组合模式矩阵(图2),技术研发强度-技术比较优势关系可以划分为I象限低-低(LL)、II象限低-高(LH)、III象限高-高(HH)、IV象限高-低(HL)四种不同的模式。低-低(LL)模式表示一国还没有进入内部创新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外部技术驱动国家创新能力成长;低-高(LH)模式表示一国已经实现了从国际技术流入向国际技术流出转变,即从外部技术驱动向外部需求拉动模式转变;高-高(HH)模式表示一国在研发强度上已经进入本土研发驱动阶段,在国际技术流动上也已经进入外部需求拉动阶段,即内驱外拉协同模式阶段;高-低(HL)模式表示一国虽然已经进入本土研发驱动阶段,同时还依赖于国际技术流入的外部技术驱动,即内外双驱协同模式。通过样本国家在图2矩阵中的位置,可以识别各国技术发展组合模式以及模式的演化路径。
2.2本土研发努力-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分析结合组合模式矩阵和G7国家相关数据,本土研发强度-国际比较优势组合模式分析结果见图3(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仅给出几个时间窗口图)。从图3可以看出,1985年美国和英国位于III象限内驱外拉协同模式,意大利和加拿大位于I象限外部技术驱动模式,法国、日本和德国位于IV象限内外双驱模式,II象限外部需求拉动模式是空白。美国的国际技术比较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主要的技术输出国;日本虽然研发强度最高,但仍然依赖外部技术驱动创新能力成长;英国研发强度不及德国和日本,但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技术比较优势。2000年的情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英国从III象限转移到了II象限外部需求拉动模式,研发强度小幅度下降,但是仍然保持了国际技术比较优势,外部技术需求成为拉动创新能力成长的力量;法国实现了从国际技术流入向国际技术流出转变,从IV象限转移到了III象限内驱外拉协同模式;加拿大和德国虽然没有出现象限转移,但是研发强度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变化,加拿大的研发强度逐步增加,而德国则呈现小幅下降。进入2010年,德国和日本双双从IV象限转移到了III象限内驱外拉协同模式。整体而言,早期的全球技术流动主要是传统型国际化模式,国际技术流动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同时只有美国和英国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技术贸易净收益,即具有国际技术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参与到创新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输出的现代型国际化模式逐步开展,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G7国家具有了国际技术比较优势,依靠外部技术需求拉动创新和经济发展。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但是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可见,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集团内部同样存在着小群体分化和国家之间的追赶问题。
2.3本土研发努力-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演化路径通过刻画在时间维度上(1985-2010年)G7国家在矩阵象限中位置的变化,揭示组合模式的演化路径,具体结果见表2。从组合模式的演化路径来看,美国和意大利的象限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意大利一直处于外部技术驱动(LL)模式而美国一直处于内驱外拉协同(HH)模式;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起点、终点和路径完全一致,均实现了从内外双驱协同(HL)模式向内驱外拉协同(HH)模式转变;加拿大试图从外部技术驱动(LL)模式向内外双驱协同(HL)模式转变,但是只在2001-2005年很短的时间内维持了研发强度在2%,很快又回到了第I象限;英国的情况最特殊,从内驱外拉协同(HH)模式转变成了内外双驱协同(HL)模式,最后又进入第II象限成为外部技术拉动(LH)模式。考虑到本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85到2010年,在此期间G7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将这些国家的组合模式演化路径进行发展阶段的排列,可以归纳出后发国家不同阶段的组合模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和经济的绝对领袖,所以在本研究时间期内,美国不仅研发强度已经进入稳定期,而且也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此时,英国已经超越了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进入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其研发强度已经难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其厚实的科研基础还可以维持其国际技术比较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局面很难维持。第二,意大利和加拿大长期处于外部技术驱动模式,虽然也试图进入内外双驱协同模式,但是研发强度一直难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准。第三,在本研究时间段内,法国、德国和日本均实现了从内外双驱协同模式向内驱外拉协同模式转变,在此之前法国、德国和日本已经经历了从外部技术驱动向内外双驱协同模式的转变。综上,将G7国家的组合模式进行排列,可以发现LL-HL-HH-LH-LL可能是一条追赶、起飞、领先和衰退的技术发展生命周期路径。在技术追赶阶段,首先通过外部技术驱动实现技术升级、获得经济增长;然后,将经济收益投入研发,提高研发强度,从外部技术驱动向内外双驱模式转变;再次,随着技术的积累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比较优势逐步显现,从国际技术流入向国际技术流出转变,从内外双驱模式向内驱外拉模式转变;最后,如果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不能持续,虽然短期内还能够维持其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外部技术拉动提升创新能力成长,但是长期来看,进入外部技术驱动模式的风险非常高。
3本土研发努力与国际技术流动的组合效应
3.1本土研发努力与国际技术流动的组合效应模型以Romer[24]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源于R&D活动的投入及其对知识存量的有效利用。2002年Furman,Porter和Stern[25]在内生增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强调世界新颖(“new-to-the-world”)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集群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关于国家创新能力以及决定因素的研究仅仅考虑了本土内生创新努力,没有考虑到国际技术流动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关学者在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技术溢出研究基础上对本土研发与技术引进进行了整合并以中国作为案例进行了实证。魏守华,姜宁和吴贵生[18]构建了中国本土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和国际技术溢出的综合作用模型。Fu和Gong[19]构建了FDI和本土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模型。在Chen和Kee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Coe和Helpman国际研发溢出模型基础上,孙玉涛和刘凤朝[26]建立了本土研发和国际溢出的整合模型。这些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的创新产出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国家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专利作为国家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运用回归方法考察本土研发与国际溢出对国家创新的影响。实际上,本土研发努力、国际技术流动对国家创新和经济产出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和直接传导作用。第一,发明专利作为国家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是TFP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从发明专利到国家经济增长还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第二,“欧洲悖论”已经充分说明了科学研究优势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成经济优势,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是需要平行追求的发展目标。第三,研发经费投入、国际技术流动以及其他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直接传导关系,可能需要经历一些其他的中间层变量,但是这个中间层变量仍然是“黑箱”,尚没有被纳入考察范围。为此,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MLPneuralnetworks)计算是一个非线性的数据建模工具集合,是基于神经元连接而成的拓扑网络系统。运用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局限,揭示本土研发努力与国际技术流动的组合效应。本研究建立3层次MLP神经网络模型即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输入层包括本土技术研发强度、国际技术比较优势、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强度、产业结构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5个变量,输出层包括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2个变量,隐含层单位数、隐含层和输出层函数由研究人员根据软件测算结果多次调试之后确定。
3.2变量指标和数据国家创新能力(TP)采用百万人拥有三方发明专利数指标。三方专利是指同时获得美国(USP-TO)、欧洲(EPO)和日本(JPO)专利局授权的专利。目前学术界通常以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发明专利作为国家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例如Fur-man、Porter和Stern[25],Hu和Mathews[27],范红忠[28]等人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USPTO专利的创新性毋庸置疑,但是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还包括了日本和诸多欧洲国家,如果仅仅采用USPTO专利可能会对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分析产生误差。三方专利数据来自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人口数据来自PennWorldTable的统计,指标时间序列为1985-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人均GDP指标。无论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⑥,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四阶段理论⑦都将科学技术创新贡献作为发展阶段描述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阶段是创新发展的基本参照系和重要产出目标,为此采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本土技术研发和国际技术流动的产出变量。相关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Bank)统计数据库。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的测算,人均GDP和三方专利的相关系数只有0.4,为此两者可以同时作为产出变量。另外,产业结构水平采用服务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指标(IS),信息基础设施采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IT),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强度采用每千名就业人员中的研究人员数(RS)。相关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Bank)统计数据库。
3.3组合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收集G7国家相关变量指标1985-2010的数据建立MLP神经网络模型,训练集(117个)和检验集(51个),总样本182个,排除14个无效样本。经SPSS17.0软件多次计算,最佳隐含层激活函数模型是双曲正切函数,隐含层单位数为3和输出层的激活函数为恒等函数。模型训练和检验的结果显示,训练集中平均整体相对错误率为13.3%,其中国家创新能力变量(TP)的相对错误率为11.7%、经济发展水平(GDP)的相对错误率为15%;测试集中平均整体的相对错误率为14.8%,其中国家创新能力变量(TP)的相对错误率为10.8%、经济发展水平(GDP)的相对错误率为19.3%。整体而言,模型达到了80%以上的正确率,基本达到预期的要求(具体结果见图4和表3)。从图4可以看出,除了本研究提出的5个输入协变量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偏差变量,并且偏差通过隐含变量产生的都为负向作用;隐含层确定了三个隐含变量H(1:1)、H(1:2)和H(1:3),同时也存在偏差变量,但是该偏差变量主要起正向作用。键结值清晰地表明给定层中的单位与以下层中的单位之间关系的系数估计值。从表3可以看出,信息基础设施(IT)与三个隐含层中间变量之间的键结值均为正,本土研发强度(RD)与三个隐含层中间变量之间的键结值中两个为正、一个为负,其他协变量与隐含层变量只有一个为正。隐含变量H(1:1)和H(1:2)与产出层变量国家创新能力(TP)与经济发展水平(GDP)之间作用关系方向相反。H(1:1)正向作用于TP、负向作用于GDP;H(1:2)负向作用于TP、正向作用于GDP。H(1:3)对于输出层变量的关系均为正向。从自变量的重要性排序可以看出,本土研发努力-研究经费支出强度(RD)的效应最为显著,其次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IT),国际技术比较优势(IA)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强度(RS)的重要性相当,产业结构水平(IS)的重要性最弱。从G7国家的经验来看,研发经费强度是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首要驱动要素,研发强度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创新能力、实现驱动创新发展,同时还是形成知识吸收能力的基础;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国际技术流入而成为创新强国;当然,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研发强度,随着技术知识的更新,技术比较优势也难以长时间的维持,英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困境。研发经费强度发挥作用的关键不仅在于达到一定的水平,例如2%,更重要的是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长期的维持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技术流动的作用不言而喻,国际技术流入可以让后发国家接受前沿知识和技术,缩小技术差距、缩短追赶时间;国际技术流出则是加快了新技术扩散,通过控制技术和知识产权获得经济利润。应该看到,国际技术流动的基础是本土研发努力,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都不能脱离本国的研发能力、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都非常重要,本土研发经费强度是一国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国际技术流动的作用虽然弱于研发经费强度,但是同样也不可忽略。
4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揭示G7国家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演化路径以及对国家经济和创新的作用,提出G7国家经验对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启示。通过G7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两个方面的简要结论。第一,由于G7国家在本研究时间段内并不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通过G7国家的组合模式综合分析,我们提炼出了本土研发努力与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模式的演化路径(LL-HL-HH-LH-LL)———外部技术驱动模式-内外双驱模式-内驱外拉模式-外部技术拉动模式-外部技术驱动模式。根据模式演化路径,中国正处于从外部技术驱动模式向内外双驱模式转变过程中,持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是关键。第二,考虑到回归模型在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组合效应研究中的局限,本研究引入了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土研发努力和国际技术流动对于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其中本土研发努力的作用约为国际技术流动的两倍,与此同时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也不可忽略。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013年全国R&D经费支出为11846.6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了2.08%,已经开始从外部技术驱动模式向内外双驱模式转变。在R&D经费强度突破2%之后,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持续的研发努力和高效的经费管理。
国家创新能力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R&D经费强度需要长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才能起到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作用,美国1957年R&D强度达到2.15%,到目前为止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G7国家的经验表明,有些国家只是在短期实现了R&D强度2%的突破,然后很快又回到了2%以下,例如加拿大;有些国家虽然R&D强度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2%以上,形成了较强的国家创新能力,但是由于研发强度难以持续,从内驱外拉模式转向了外部技术拉动模式,例如英国。为此,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维持R&D经费强度在2%以上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通过立法等途径强制实施这一战略举措。R&D经费强度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持续的R&D经费强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高效配置。本土研发努力的关键是要将R&D经费支出转化为知识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吸收能力,国际技术引进才能被消化吸收,并转化为本国企业的内生技术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本土研发努力实现再创新,进而可以将新产品和新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实现从内外双驱模式向内驱外拉模式转变。目前,我国的研发经费中还存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投入不均衡、重发展轻基础和应用研究、研发经费使用不规范等多方面的问题[29],在R&D经费强度快速提高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R&D经费管理。具体而言,需要转变过度依赖研究机构特别是中科院系统,执行政府R&D经费的问题,同时强化企业在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中的作用;提高应用研究强度,建立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之间的纽带,实现R&D链条的综合集成;提高基础研究经费中人员费的比例,提高基础研究人员的待遇,稳住基本科研队伍。
作者:孙玉涛 张帅 尹彤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