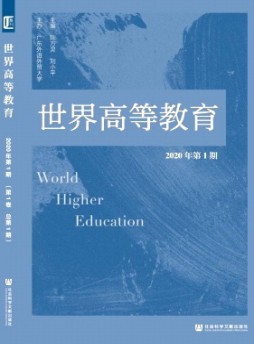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估算方法介绍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如),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六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6],结果如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五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六国中,美国在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与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以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2•高教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把中六国三个时间段(1913—1950年、1950—1973年、1973—1984年)的人均高教年限年平均增长率与GDP年平均增长率的18对数据放到一起来考察,从发展历程上看,可以发现六个发达国家除日本之外,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率全部呈加速度增长,而相同年间的GDP增长速度却有升有降,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代里,往往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速度减慢,GDP增长速度比较慢的年代里,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年增长速度相反加快。例如美国人均高教年限年增长率1913—1950年间为2•22%,1950—1973年间则增长为3•01%,到1973—1984年间进一步增长为5•60%,相同年间的GDP增长率依序分别为2•78%、3•72%、2•32%。使用SPSS软件计算上述六国三个时间段人均高教年限年增长率与GDP年均增长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027,小于0•1,显著性水平P=0•916,远大于0•05,说明二者根本不相关。由于一国人均高等教育年限的高低代表着该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因此,可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高教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同的,也是不相关的。当经济快速增长,就业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时候,许多人就去工作,受教育的人数和人们受教育的时间就会减少,高教发展速度就会下降;相反,当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人们的教育需求量就会增加,高教发展速度就会上升,规模就会扩大。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弹性高教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调节器和助推器。
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有效经济需求不足,失业率加大的时期,急需启动高等教育这个“调节器”和“助推器”。然而,由于我国的高教产业体制一直过于刚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直很低,急需改变这种状况。为此,必须一方面加快高教发展速度,扩大高教规模,通过增加教育服务的消费和提高全民科教素质,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一方面深化高教体制改革,提高高校内部效率,使之与市场经济接轨,迫使多种形式的高教组织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使其成为我国举步维艰的市场经济的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