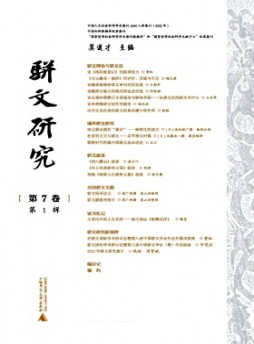骈文隶事及其深层文化意蕴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骈文隶事及其深层文化意蕴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齐鲁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隶事与南朝骈文形式美
隶事即数典用事,亦称用典,与对偶、藻饰、声律共同构成了骈文追求形式美的四大要素。南朝时期,数典隶事之法颇受文家青睐,自颜延之、谢庄、鲍照至任昉、王融、沈约,再到徐陵、庾信,隶事技巧愈趋精湛,风气亦盛极一时。关于隶事的种类,《文心雕龙?事类》分成用于征义的事典和用于明理的语典两大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1](P614)此种分类方式为后代广泛接受。骈文隶事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艺术表现力,又可增强文章形式的典雅、委婉、凝练、对称之美,体现出明显的装饰性功能。台湾学者张仁青论骈文用典的必要性及表达效果说:“骈文之繁用典故,自魏晋以后成为必要之条件……文学作品之用典者,无间中外,所在多是……是以典非不可以用,只看各人能不能用,善不善用,诗文修辞之法,不止白描一端,固夫人而知之者也。抑更进一步言之,骈文为唯美文学之一种,亦即属于美感之文学,不可不著重词采,其来源皆取材于典籍故实,读书稍多,造语自有来历。骈文原是间接表达作者之意念,魏晋以前多用排比,魏晋以后乃用典实,其作用在于用简洁之文字表达繁复之意思,使作品富有浓厚的神秘性、象征性与趣味性,以增加读者之美感,从而提高其艺术价值。”[2](P137—138)近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则说:“文家用古事以达今意,后世谓之用典,实乃修辞之法,所以使言简而意赅也。故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约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骈文用典既能借助象征隐喻手法使文章更显含蓄委婉,又能通过丰富多彩的华词丽藻加强藻饰之美,还能凭借两两对出的古人古事令文气畅达充足而又可收束,其妙处于此可概见。数典隶事与藻采、对偶、声律一样,在南朝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隶事用典都经过精心的字雕句琢,故藻采纷呈,对仗精工,语词简洁精当,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藻饰、对称及凝练之美。姜书阁在叙述骈文形式特征时,曾将用典与雕藻合一并加以解释说:“这是两回事,但又密切相关,所以也可以当作一条来说。用典使事本是为了借古明今,以彼喻此,散体文章也需要,原非骈文所独具;饰词琢句,在没有骈体以前也是经、史、诸子之文所不废的。然而,这两项之所以成为骈文的特征并为论文者所公认,则是由于骈文为美文、为丽辞,为排偶对仗之作,故襞积典事,炼词铸句,不但较写散体文章之可以用白描者不同,而且必须为了适合上下联长短、平仄、虚实等属对的要求,在用典的方法上和造辞的技巧上也因而有所不同。散文用事,可详举某一旧典,不限字数,亦不须另取一事与之对称;骈文则往往一句一典,若其事甚繁,则裁剪为难,遂不免意晦辞艰,故作者必须精加雕琢,以成藻采。”范文澜则将用事与对偶并论:“对偶与用事是不可分的,没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对不起来,就是对起来,也只能称为‘言对’,属于低级的一类。”概言之,骈文隶事可与雕藻、对偶及声律同行,意图皆在于加强文章的形式美。刘宋以降,骈文追求繁密用典、丽藻缛绘及精工对偶,风气颇为兴盛。以颜延之而论,世称其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尤为繁密”、“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7](P881)、“错采镂金”、“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对偶”[5](P412),其文亦然。所谓“侈言用事”[8](P89)、“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织词之缛,始于延之”[9](P64)、“文章之美,冠绝当时”[10](P1891),都是对颜氏骈文注重隶事与藻采的准确概括。稽考颜延之《陶征士诔》、《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祭屈原文》、《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诸文,无不以用典与藻饰贯穿全篇。到了任昉、王融,仍然“竞须新事”,导致“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6](P4)、“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11](P908)。骈文创作中注重用典、对偶与藻饰的现象极为普遍,而且还常常得到赞赏,如萧纲即称赞用典繁密的“任昉、陆倕之笔”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12](P691)。任昉长于属笔,为齐梁骈体大家,其文巧于隶事是优点,但隶事过多又成了最大的缺点。清人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一评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云:“专以隶事见长。”“愚谓用事不显是彦昇长处,专以用事见长是其短处,得使事之妙而不得不使事妙,方之诗家,如李玉谿。”[13]孙月峰则评此文曰:“以造语胜,其用事却俱不显,故自妙。”[14](P723)又评任氏《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云:“以用事见姿态,然亦是活用,不是板用。”[14](P724)孙德谦《六朝丽指》说:“《诗品》云:‘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然则彦昇之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谓其文亦然,皆由于隶事太多耳。语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若事事征实,易伤板滞。后之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然而任、沈要为骈文大家也。”[总体看来,任昉骈文以用典精妙见长,虽多用典却不滞于典,而是熔铸锤炼,化繁为简,且能融入散句以疏通文气,故平易自然而不使人觉察。与刘宋初期骈文用典多以明用或直用为主不同,齐梁以后用典方式则走向多样化,明用之外,又有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等。永明声律论提出后,骈文家在隶事的基础上又讲究平仄格律,寻求声律之美。观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各体骈文,即可见其声律之严谨细密。
降至徐陵、庾信,骈文臻于成熟,藻采纷呈,用典繁密,可谓“词事并繁”[9](P64),加之对偶精工,声律谐调,句法灵活,以四六为主而兼有其他句式,在形式方面堪称至美。“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5](P416)。作为加强骈文形式美的一种重要修辞方式,徐、庾之作对隶事更是刻意经营,数量众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但并不给人殆同书钞之感,反倒觉得如出胸臆。究其原因,就在于徐、庾隶事善于灵活化用,熔铸无痕,巧妙妥当而又平易自然。如庾信《谢赵王赉丝布启》:“妾遇新缣,自然心伏;妻闻裂帛,方当含笑。”巧妙化用乐府古诗《上山采蘼芜》与《帝王世纪》所载夏桀后末喜、《通鉴外纪?周幽王纪》所载幽王后褒姒爱听裂帛之声的典故,以古比今,出言平淡,宛如常见叙述,用典而不着痕迹。再如徐陵《玉台新咏序》:“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柙。”初看只是寻常写景,其实二句皆暗用《汉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树,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花子青赤,以珠玉为之,空其中如小铃,锵锵有声。又以白珠为帘,玳瑁柙之。”以汉武宫中的瑰丽奢华景观比拟梁代宫廷的豪华壮观之景,用典自然平易,近于白描常语。又如庾信《哀江南赋序》:“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上联出自《后汉书?冯异传》:冯异不与诸将争功,独自躲在大树下,被称为“大树将军”。庾信借用此典,仅取其语词,意在说明侯景之乱时,自己率兵抗拒却溃败于朱雀航,其地失陷,故有飘零之义。下联借用《战国策》所载荆轲离燕赴秦刺杀秦王失败而身死之事,言己出使西魏而不得归的凄凉状况。翻检徐、庾各体骈文,隶事无不灵活巧妙,堪称“缉裁巧密,多有新意”、“使事跌宕”、“运事甚巧”(P706)。善于突出数词的作用,以增强表达效果,也是徐、庾骈文用典的一大特点。如徐陵《玉台新咏序》:“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庾信《谢赵王示新诗启》:“八体六文,足惊毫翰;四始六义,实动性灵。”徐陵《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羌胡宝马,纵横七泽之中;荆楚楼船,弥满三江之上。”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夷歌一曲,未足消忧;猿鸣三声,沾衣无已。”徐陵《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迁箕卿于两馆,絷骥子于三年。”庾信《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蓬莱谢恩之雀,白玉四环;汉水报德之蛇,明珠一寸。”徐、庾文章中的数词不但数量多,而且在文中的位置也灵活多样,句首、句中、句尾皆可。将数字镶嵌于精工对偶与恰切用典中,益发增强了骈文的形式之美。
二、南朝骈文隶事的深层文化动因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隶事在南朝骈文创作中极为常见并且颇受称赏。追溯原因,不仅在于其独特的表达效果,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即除传统文化观念背景下的尊经崇古心态使然外,还受南朝时期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和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南朝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具有广博的内蕴和深厚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其中,尊经崇古的文化心态对于骈文隶事具有明显而直接的推动作用。先秦时期的两大主要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为后世文人留下了许多权威而经典的文本资料,这些都成为骈文隶事素材的重要来源。两汉时期,先秦儒道著述被奉为经典,崇古尊经的心态促使文人在创作中屡屡引经据典。魏晋以至南朝,尽管儒学的地位已经动摇,两汉时期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但文士信古崇古的心理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了。先是东晋中期以后,玄学、佛学合流,士人清谈的内容自然包括玄学和佛理。至刘宋,则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并列,此外,佛学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此时经典文本的范围也得以拓宽,由儒道典籍及其注疏类著述延伸至史、子、集、百家杂记、逸史轶闻,甚至外来典籍如佛学著作等。文学批评家论及文章产生的源头时,往往追溯至早期的儒家经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自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至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无不持此说。这一观点恰恰说明了文章与古代典籍的密切关系,亦从侧面印证了文人尊经崇古心态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崇古信古心态的驱使下,骈文中出现大量隶事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南朝文士因受前代清谈与玄学之影响,作品遂由情韵之表现,转为事理之铺陈,而又处心积虑,欲在修辞技巧上突过前人,于是吐胆呕心,全力经营,因而造成用典隶事风气之全盛,使诗文形式完全改观”[2](P142)。稽考南朝各家各体骈文可见,其隶事多来自《诗经》、《楚辞》、《尚书》、《论语》、《礼记》、《中庸》、《孟子》、《老子》、《庄子》、《列子》、《管子》、《吕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臧荣绪《晋书》、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书》、《晋中兴书》、《宋书》、《南齐书》、《西京杂记》、《淮南子》、《法言》、《说苑》、桓谭《新论》、《抱朴子》、《竹林名士传》、《博物志》、《搜神记》、《世说新语》、《山海经》、《穆天子传》、《荆楚岁时记》、《三辅决录》、《孝经钩命決》、《维摩经》、《维摩经注》、《涅槃经》、《大智度论》、《瑞应经》、《妙法莲华经》、谢灵运《金刚般若经注》、《僧肇论》、《大品经》、《高僧传》以及诗、赋、各体散文与骈文等,可谓经史子集、百家杂记、佛学典籍,一应俱全。南朝骈文隶事数量多,范围广,时间跨度长,技巧高超,为后代骈文隶事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骈文通过隶事来加强形式美也反映出南朝文学重形式的审美取向。汉末魏晋以降,重形式的文学思想日益发展,时至南朝,随着骈文逐渐走向成熟,追求形式美的风气臻于极盛。论者一再指出:“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刘宋至陈,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果从大的脉络考察,它一直是沿着自建安开始的重文学特质、重抒情、重文学形式的探讨的方向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骈体文章发达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骈文要求文章讲求对偶、辞藻(包括比兴、夸张、字形等等)、用典、声韵等语言美;南朝文人关于文章美的衡量标准,正是首先从这些方面着眼的。”[隶事与对偶、藻饰及声律皆为南朝骈文增强形式美的修辞方法,因此颇受当时文学批评家的赞赏。刘勰对魏晋以来日趋发展的骈体文学持肯定的态度,对隶事、骈偶、辞藻、声律等骈文形式美的诸要素都很重视,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各设专篇予以论述。据《文心雕龙?情采》所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为形文,即五色,五色交错而成文采;二为声文,即五音,五音排列而成乐曲;三为情文,即五性,五情并发而成文章。《文心雕龙?原道》提出,形文即文采之美,它广泛地表现于自然界万物身上,日月山川和各种动植物都有形态色泽之美;声文即音乐之美,如风吹树林、泉水激石等所发出的美妙音韵。人类制作或加工的事物的文采,主要也是表现在形状、声音两个方面,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文心雕龙?附会》认为,作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论及骈文的隶事用典、藻采与声律,分别以人的骨髓、肌肤与声气作比,较为贴切。辞采指形文,宫商指声文,故《文心雕龙》立《声律》一篇专论声文,立《事类》、《丽辞》、《比兴》、《夸饰》、《练字》、《隐秀》诸篇,分别论述隶事、对偶、比喻、夸张、字形、含蓄和警句等修辞手段,这些都属于形文。无论形文还是声文,都是骈文讲求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刘勰外,还有不少批评家对骈文隶事、藻采等持肯定或赞成的态度。钟嵘虽反对诗歌大量用典,但对骈文隶事基本上还是认可的:“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萧统《文选序》言选文标准曰:“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同样不外乎注重隶事、藻采等增强骈文形式美的诸要素。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一文也考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很显然,通过大量隶事来加强骈文文采,是十分有效的,“当时大多数文人认为,大量用典,是增加骈文文采的一个重要手段”。重视形式之美的文学取向对骈文隶事的促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南朝骈文多数出自门阀士族阶层和朝廷重臣之手,这也是南朝文学历来被视为贵族文学的主要原因。贵族文士为炫耀深厚的家学积淀和博富的学识,在诗文中竞相借助数典隶事来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文学创作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过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又助长了这种矜才逞博的社会文化风气。探讨南朝骈文隶事的深层文化动因,自然离不开当时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尚对骈文家的影响这一因素。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由来已久。按《颜氏家训?勉学》所载,魏晋以来,士族文人多笃于学业,以增进学问为维持家学门风和立身的重要手段:“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在这种风向的指引下,博物洽闻遂成为众多文士共同追求的目标:“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
关于此类崇尚博学的作风,史书中更是不胜枚举。据《南史?王准之传》所记,准之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并熟谙江左旧事,自是家世相传,形成一门学问,因缄之于青箱,故世谓之王氏青箱学。又如徐广家世好学,至其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见《宋书?徐广传》)。刘峻家贫好学,寄人篱下,读书通宵达旦,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称之为“书淫”(见《梁书?文学下?刘峻传》)。江总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常昼夜寻读,未尝辍手(见《陈书?江总传》)。陆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尤好《汉书》(见《陈书?陆从典传》)。又《南齐书?王僧虔传》载《诫子书》曰:“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高门士族告诫后辈勤于读书治学之苦心于此可见。学风的兴盛也引发了文人聚书藏书和借数典隶事以逞才显博的风气。沈约、任昉、王僧孺并称梁代三大藏书家,正是因为有广览群书作为基础,他们才能有博富的学识以助于大肆数典隶事。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约尝侍讌,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隶事是炫耀博学的一种方式,在熟记关于栗的故事这一点上,梁武帝萧衍与沈约为显才学,各不相让,终致反目,而沈约也差点因此受罚。这种帝王与士族文臣以隶事争胜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当时崇尚广博的学风。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显然,任昉“才思无穷”应得益于博览群书。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又如姚察“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南朝文人崇尚学识富博,“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而隶事正是逞才炫博的最佳方式。于是,一时之间,竞相隶事之风大盛,而王俭文学集团最负盛名。《南齐书?陆澄传》:“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又《南史?王摛传》:“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竟陵王子良校试诸学士,唯摛问无不对。”尽管何宪“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但与陆澄、王摛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于此可见当时隶事高手之间相互竞赛的精彩场面。通过隶事来显示才学多寡,文士对此极为看重。作为帝王或文学集团的首领,一方面奖励高才博学者,另一方面对于胜己者却又不能容忍。除上述沈约因隶事而得罪梁武帝萧衍之外,“博极群书,文藻秀出”的刘峻也因才高而遭到萧衍的贬抑。《南史?刘峻传》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梁武帝还曾敕命张率撰妇人事多条,勒成百卷,亦见张氏颇悉典事。又沈约任丹阳尹时,曾于座测试刘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受到陆倕的高度赞赏。陆云公好学有才思,自小博观众书,陆倕、刘显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刘显甚为叹服。韦载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韦稜见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诸如此类博学强记、熟谙典事之例见录于史籍,可谓俯拾即是。文人要想在数典隶事竞赛中取胜,无疑要依赖于自己富博的学识,但个人的记忆力与知识储备毕竟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南朝时期出现大量类书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书的问世为隶事提供了诸多便利,显然又会推动隶事之风愈演愈烈。“按隶事与类书乃互为因果,用典多,则类书必应运而生,类书多,则用典之风愈盛,作者不复以自铸新词为高,而以多用事典为博矣”。最早的类书为魏文帝时撰集的《皇览》,其后屡有继作,极盛于梁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据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及《三国志?魏书?刘劭传》可知,当时儒生王象、桓范、刘劭等皆参与了编纂《皇览》。撰集类书最初是为了博览检阅的方便,后来却成了属文时猎取辞藻、缀辑典故的宝库。“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据《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杂家书(含不录撰者)共97部,其中南朝人所编撰的有《纂要》(颜延之撰)、《四部要略》(萧子良等撰)、《袖中记》(沈约撰)、《珠丛》(沈约撰)、《采璧》(庾肩吾撰)、《锦带》(萧统撰)、《类苑》(刘峻撰)、《华林遍略》(徐僧权等撰)、《法宝联璧》(萧子显等撰)、《长春义记》(萧纲等撰)等50余部。这些类书撰集的经过多载于史书,因此可信度较高。如《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又《梁书?文学下?刘峻传》:“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此事亦见于《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齐梁时期编纂类书的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端。数典隶事为南朝骈文的一大构成要件,它不仅反映出文士崇古尊经的心理,而且也推动了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和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赵红 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