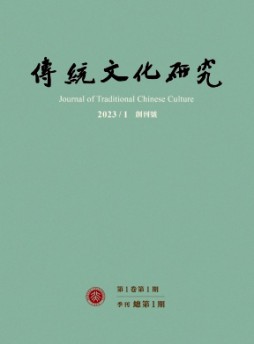传统音乐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传统音乐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对于多数青年学者而言,要实现这个跨越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有跳出音乐小文化圈进入国家历史大文化的宏观学术视野,更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不畏艰苦深入实地考察的学术勇气。项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产生的学术意义异常深远。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的各种音乐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专著《山西乐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种方法相联合的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其间必然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但遗憾的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大一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到了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轮值轮训制,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
项先生曾多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无序的。其实不然,一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例如宫廷教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没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中存活。因此,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页)、《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35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纵观整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血肉联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立地看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之形态——音乐本体,而忽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过头来,文史学者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与范畴,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景使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影响。基于此,项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概念。项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礼五礼)与乐的对应、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文化的功能性内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类礼乐的使用范围,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礼乐笼统论之。
“以乐观礼”,只有对礼中用乐的等级观念有深层把握,明了同一种礼制,哪些等级能够用乐?明了礼制本身的差异性,才能够看清楚乐之于礼的严肃性和丰富性;只有对国家礼乐如何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的过程作出梳理,并对当下民间礼俗如何承载、接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礼乐作出合理判断,才能够对当下全国各地广泛存在的传统用乐形式、不同乐队组合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当数量乐曲的属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历史上国家礼乐承载群体的整体把握是认知“以乐观礼”的关键之一,南北朝以降乐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礼乐实施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对上述问题均需钩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则,这种论礼乐而混沌的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改观。[4]
换言之,只有对封建礼制的功能与本质,礼与乐对应的内在意涵和互文关系[5]有正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联系的理念,全面客观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传统音乐文化事像中的某一个案和音乐品种。
此外,在论及古代礼乐制度与各音乐形态的意涵与互通方面,项先生论述颇多,如《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页)、《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页)、《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黄钟》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等,皆属于这一学术论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夯实本学科的研究基础,推动本学科的健康发展。一门学科欲获得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时性过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间肯定会面临新旧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择与扬弃。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引入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更新和壮大自己的学术生命。
以音乐史学为例,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了,近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的方法论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原有的研究结论与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当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把握愈来愈多的学术事像,无法对新生的学术难题[6]作出合理的阐释时,我们该如何抉择?正如项先生在《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一文(《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页)中指出的那样,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的理念增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音乐史学发展的贡献尤甚。接着,作者谈到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认为既有的音乐史学论域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欣赏的意义,而弱化了中国历史上音乐既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丰富内涵。如此则很难反映中国音乐在历史语境下的整体样貌,诸如音乐的存在方式、国家礼乐的上下贯通、民间对于国家礼制中吉礼理念与国家礼乐中礼仪用乐的重新组合与拼装、在“为神奏乐”理念下相当古老的音乐形态可能近乎原样承继于当下。项先生建议从社会整体把握的视角,以国家礼制下的多功能性用乐为主线写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国家乐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礼乐文化史。认为对乐籍制度和制度下群体承载的探研,应该成为一个相对长历史时期音乐史学把握的重点。
在此理念下,才能够认知传统社会中主导层面制度下创乐和用乐的整体一致性和体系化,继而看到在这种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动态延展性和差异性。项先生指出,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展开,并呼吁广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第2篇
最常用的是音画同步,即用音乐来复述、强调画面的视觉内容,音乐与画面的情绪、节奏一致,视听统一。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用音乐直接表现画面的情绪、气氛,由此产生了音画对位的结合方式,即音乐所表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与画面中所呈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反衬,烘托出画面的内容。这种结合方式有利于音乐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影片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对其进行评价,并不是以音乐的音响效果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体现了影片的总体构思为准绳。电影音乐首先应该是属于电影的,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符合电影的观念和需要,无论是主题创作音乐,还是资料性音乐,都必须与影片风格统一,与叙事节奏相辅相成,与电影其他的元素相匹配。电影音乐的结构形态语言以及长度,都必须由电影的要求来决定,而不能离开影片孤立地强调音乐的表现性和完整性。总之,电影音乐必须是为电影的整体要求服务,并自然地发展和分寸适当地存在。只有设计自然,在审美主体不知不觉中起作用的电影音乐才是电影音乐的上乘之作。
电影音乐具有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功能
在电影艺术中,音乐和视觉影像时时刻刻都在描绘着特定民族的风俗、信念与习惯,传达着知识、艺术、道德与法律的信息,暗示着一种历史的与人文的气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自身民族文化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个群体的心灵状态、习惯与性格特征,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生活状态的整体显现。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是一种从学习中得到的行为方式,也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有的。
电影音乐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往往是以音乐主题的方式实现的。音乐主题是影片音乐的“核心”部分,是描绘人物形象最突出、最富于乐思的旋律与节奏。美国电影理论家迈克尔?拉毕格在《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中说:“一种特殊的管弦乐法或特殊的音乐节拍贯穿整部电影是由角色、场合或情绪所设定的。”电影音乐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不是理性的诠释,而是感性的刻画,是通过感性的节拍、旋律、节奏以及不同器乐音色的特点来描写人物文化传统与性格特征的。在电影音乐中,不同的乐思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与立意,不同的乐器拥有不同的地域色彩与特性,这种旋律的立意与特性不仅能够突出人物情感和性格的特质,也能为某些场面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民族的氛围。例如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的影片《廊桥遗梦》中,导演在两个主要的场景里通过收音机传递出来的、有声源的意大利歌剧音乐交代了女主人公弗兰西斯卡的出生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物的兴趣、品味,并通过歌剧音乐刻画出主人公内心那种多情浪漫的性格特点以及她美好的个人理想与沉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影片中这对男女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具有人物性格上的依据和可信性。
第3篇
关键词:传统审美;“中国风”音乐;文化传播
近几年来,一批新生代音乐创作人和歌手将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流行音乐。这种新奇、独特的音乐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乐坛,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大众,将“中国风”音乐的风潮推到了极致。同时,这种“中国风”也在广告、电影、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文化。可以说,“中国风”的流行,与在儒、道、佛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现象也源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一、何谓“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如果按字面上解释,即有中国特点的音乐风格。当然,这并非是指中国的传统音乐,而是指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一种融合传统音乐的独特音乐形式。关于“中国风”音乐的定义,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音乐人黄晓亮在博客中说道:“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也有人曾经试着给“中国风”音乐下过如下的定义:“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在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在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传说故事。虽然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风”音乐的特质。
(一)歌词包含中国古典文化
“中国风”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歌词中包含中国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辞赋拿过来运用,如王菲的《水调歌头》、蔡琴的《如梦令》、伊能静的《念奴娇》等,即是把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并融入现代配乐来重新演绎。有的作品则是借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镜”、“梅”、“竹”、“兰”、“茶”、“杨柳”等融人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等。还有的作品传达了中国传统的情感内容,如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听妈妈的话》、《蜗牛》等,这些歌曲显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伦理情感紧密契合。有音乐人指出:“‘中国风’音乐作品的歌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歌词整体营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围,运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词中带有一些鲜明的民族符号,以此来体现民族特色。
周杰伦的代表作《东风破》,其歌词是:“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词牌名,其中“离愁”、“烛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满古典意象的词语更是营造出悲凉的气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临摹”、“窑烧”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词被巧妙融合在歌词中,同时极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内容。《本草纲目》借用了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来传达古典情怀,胡彦斌的《曹操》则描述了一代袅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传统文化是“中国风”音乐在歌词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二)编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乐特征
一般来说,当代流行音乐习惯以西洋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和电子音乐为主,而“中国风”音乐使用传统的乐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筝等,使中国韵味被积极地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音乐表达。如周杰伦的《东风破》主要运用了二胡;《霍元甲》则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闷而厚重的鼓声阵阵,表现一代宗师的武学气概,全曲气势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运用了箫,箫声绵绵,流畅抒情,委婉动听。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乐和编曲之外,很多“中国风”音乐大胆地运用了传统音乐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戏曲唱腔等。如陈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红尘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边》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说》则引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两种音乐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让人耳目一新。随着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和宋祖英两种不同音乐形式的巧妙融合,这种“混搭”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三)整体风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重要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曲乐,都讲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绵长深远,含蓄朦胧。
“中国风”音乐无论在歌词、编曲、唱法、旋律还是MV的拍摄上,都注重使音乐整体上能够展现出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中国风”音乐多采用古典诗词作为题材,情感表达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同时,曲调的悠扬和谐也体现了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观。除此之外,MV的拍摄也体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要求。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存在着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在美学的层面上,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将审美意象作为“情感符号”和“艺术幻象”来考察。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朗格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出发,认为艺术意象也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在“中国风”的音乐中,充满了类似的传统意象,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群带纷飞。“烟雨”、“青花”、“素胚”、“芭蕉”、“门环”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扬的曲调和水墨风格的唯美的MV,组合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种欲说还休、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二、“中国风”音乐背后的古典审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所谓审美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审美文化所独自具有的内在审美气质和性格,它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艺术态度的核心因素,属于一个民族文化比较深沉的东西,与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相一致。审美精神一旦形成便会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地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及审美的发展。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是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以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精神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音乐学者林华先生就曾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我们的审美个性中,既有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积淀成份,同时又有受到民族审美意识影响的成份……”。
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其核心的哲学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促使中国古典艺术强调“道”、“气”贯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识,注重直观感悟的生命体验,同时还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想价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识构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内在特质。中国艺术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个体生命和对象,而是生命的整体感、流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审美精神导致中国古典审美重神韵、气韵、气势、气脉、气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现宇宙无限的生机活力。这种审美精神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尽管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以西方音乐形式为主流,但这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审美精神要求也呼唤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的音乐形式出现,而“中国风”音乐正是符合了中国人内在的审美要求。
同时,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中,礼义廉耻、中庸之道、重亲情、尊伦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使人们在潜意识当中钟情于写意的古典歌词,倾心于传统的民间乐器,醉心于含蓄、内敛的情感等等。在欣赏“中国风”流行音乐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怀,使听众很容易就和音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中国风”音乐带来的反思
对于艺术领域中的这种“中国风”现象,很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审美标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传承五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消费时代,任何文化行为只有在转化为商业行为的消费中实现对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才能被公众更多地关注与接受。而“中国风”音乐无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它通过特定的商业传播手段和商业行为方式,使文化消费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愉悦,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传播。由此看来,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 上一篇:声乐教育教学论文范文
- 下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